剧情简介
别名:O先生的故事,Yin乱横行于八月巴黎的艳阳天。女友想生小孩吓出一身汗之后,O先生沉溺于找到理想性-伴侣,美其名曰街头性观念调查,十三个女郎,十三回邂逅,O先生的马拉松ML愈跑愈劲,终至万劫不复hellip;hellip;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5796.html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革命不需要从容不迫,革命当然也不是改良主义,当一切温和的行动在革命中被否定,革命指向的只能是暴力,而且是以暴制暴。开场的这句引语在最后得到了生动的阐释:当一列火车冲向了满载着政府军士兵的列车,激烈的爆炸是一次暴力;当革命队伍中的医生因为出卖同志而葬身事故,燃烧的火焰是一次暴力;当胡安连续的射击杀死了幸存的上校刚特,过瘾的枪杀也是一次暴力……在暴力完成之后,受伤的约翰要了一支烟,面带微笑,当胡安问他:“如果你离开了我,我该怎么办?”约翰说:“你会当上将军。”然后将一枚皇家十字架勋章送给了他。戴上皇家十字勋章仿佛是胡安成为将军的一次加冕礼,当革命在暴力中结束,他们是初战告捷的胜利者,但是当胡安说要找人帮忙的时候,为什么在他转身想要离开的时候,约翰却制造了一次爆炸?在浓烟中,在火焰里,一个革命者死了,留下单独的“将军”如何引导一场革命?仿佛革命戛然而止,出现的片名又在解构着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革命:Duck You Sucker——是“起开、二球”,是“你丫爬下”,是“低下头去”,甚至是“A Fistful of Dynamite”的“一把雷管”——不是崇高的革命行动,不是深刻的阶级暴力,它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让革命变成了仅仅是“一把雷管”的暴力。在最后的暴力中,死亡是仪式还是命名“将军”是仪式?或者说,谁是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人物?约翰在炸毁了列车上的叛徒,在目睹了镇压革命的上校被打死之后,他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脑中闪现的是和女友、和朋友在一起的浪漫“往事”:他们在树林里奔跑,在阳光下嬉戏,然后他吻着漂亮的女友,在两个人相拥中,朋友在旁边看着他们,然后女友又走到朋友身边,两个人也开始相吻,而旁边的约翰脸上露出了会意的笑容。三个人的往事,三个人的情感,也是三个人的爱情?约翰吸着烟露出的笑容将这一幕回忆变成了人生最后的定格,而当他最终按下爆炸的开关,也一定是完成了人生最后的仪式,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痛苦,而是欣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他完成最后的行动,革命对于他来说只是回归到没有恩怨的三人世界。三人世界,完全是私人的往事,完全是个人的故事,作为胜利者,也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复仇,所以约翰的革命是只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而当他命名胡安是英雄的时候,革命是不是在这样的命名中会开始新的征程?胡安不想他死,当然对于约翰的自我爆炸感到突然,但是在他听见爆炸而回望的时候,当他看见约翰消失于漫天的浓烟中的时候,他没有悲痛地大声喊叫:“不!”眼神里分明有着一种对于约翰行为的理解,无论是被称之为将军,还是那枚皇家十字勋章,连同最后理解的眼神,都成为在革命往事之后新的起点,都成为在“一把雷管”之后新的使命——至少在莱昂内的电影叙事里,一次爆炸就是一种续承:约翰用一次爆炸完成了自我革命,他把更高的革命使命交给了胡安,而胡安从劫匪到英雄,再到被命名的“将军”,将在浓烟散尽之后投入更激烈的暴力推翻的历程中。但是,让一个从来没有革命意识的胡安承担革命的使命,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讽刺?或者说,在胡安被约翰命名为将军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在对约翰的理解中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这必须从“革命往事”中展开对真正革命者的考量:在“一把雷管”开启的故事里,有两个用暴力革命的人物,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胡安。如果从革命者的身份来说,约翰更像是引导胡安走上“将军”之路的引路者,他身上携带的炸药,是对于胡安枪支的升级,他乘坐去往梅萨维多的火车,是对于胡安流浪甚至骑马的升级——的确,约翰在武器、交通工具上,都是一个在胡安眼中的革命者,也正是他的出现,使得胡安慢慢从劫匪变身为一个经历了暴力的“英雄”。当然,约翰还有更多的革命意识,他在梅萨维多的小酒馆里对胡安说:“如果这是场革命,意味着混乱。”这是胡安第一次听说革命,但是对他来说,来到梅萨维多只是为了抢劫银行,当在约翰的炸药作用下胡安冲进了银行,以为在这里会拿到无数的黄金,但是最后收获的却是150名政治犯,约翰对他说:“这里的钱一个月前就被转移了,这里只是一个政治监狱。”胡安生气地说:“我现在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骗人。”不是胡安作为流浪者、作为劫匪的骗人,而是约翰作为革命者的骗人。所以在约翰再次对他说起革命的时候,胡安说了一句:“这不是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只是我的家庭。”约翰于是对他灌输革命的理念:“你的国家也有果园,也有政府,也有地主,也有警察,也应该有小小的革命。”革命涉及到的是果园、土地、制度,针对的是不合理的政府、镇压的军警,所以在受压迫中,在不合理中,只有革命才能达到目的。约翰投身在这个不是祖国爱尔兰的革命事业中,也是一种超越了国家的革命行为,变成了国际主义的革命行动,但是当他在胡安面前扔掉了那本《革命》的时候,实际上作为革命者他其实是缺席的,他的行动似乎并不在所谓的国家层面,更不在国际层面,他只是为了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革命。从约翰出现在胡安面前,到和胡安一起解救出政治犯,再到革命组织里,以及和胡安一起实施针对镇压者刚特的革命行动,莱昂内只是在一种形式上让约翰成为一个革命者,作为爱尔兰革命军的爆破专家,他辗转到墨西哥和美国,仅仅是为了了却自己的心愿:杀死叛徒。他在镇压者处决革命者的现场,看见了革命队伍中的医生,正是在他的指认下,那些革命者被处决,所以他脑中闪现的是自己在酒馆里被好友指认的回忆场景:警察带着他的朋友来到酒吧,让他指认里面的每一个人,但他点头,里面的人就被带走,而背对着他的约翰是透过面前的镜子看见了叛徒的丑陋面目,曾经是并肩作战的同志,曾经是三人世界的好友,却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于是最后的最后,约翰转身,藏在身上的机枪射出了仇恨的子弹。杀死叛徒,这是一种革命行为,所以在这里,约翰也杀死了出卖同志的医生,就像医生和他在一起问他的那样:“你叫上我只是为了杀死我?”约翰的回答是:“我不审判你,我只相信炸药。”他是给了医生一个机会,在列车疾驰冲向政府军火车的时候,他让医生和他一起跳,但是最终医生没有跳下火车,在相撞的爆炸声中这个叛徒葬身在火海。而对于约翰来说,这一次暴力行动便是他最后的革命行动,因为叛徒被消灭了,他曾经的仇恨也便消失了,于是微笑着,于是把胡安命名为革命者,在自我革命中安然走向死亡。所以在整个过程中,约翰的革命行为都只是在私人立场中展开,他如何成为爱尔兰革命军一员,革命军如何受到镇压,他又如何辗转到了美洲大陆,又如何加入革命组织,似乎都不再重要,甚至莱昂内让他对“往事”的回忆中,也完全局限在私人恩怨上:从最初三个人开着车行驶在路上,女友和他激吻朋友欢快开着车;到后来朋友成了叛徒,他一枪干掉了他;到最后闪现三个人又在一起上演浪漫结局——往事只是个人的往事,从在一起到叛变,从消灭叛徒到又在一起,在这个回环中,革命的意义和使命完全被消解了。约翰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意识上并没有脱离个人主义,所以他的革命性是不充分的。相反,胡安这个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他走上革命却具有某种样本意义。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本和资产的流浪者,甚至是一个在富有阶层面前丧失了尊严的人,马车上乘坐的人是贵族,是神父,是富婆,他们把邋遢的胡安叫做畜生,说他没有自己的父母,说他是地下室的老鼠,这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革命最初的萌发:即使胡安过着打劫的日子,即使被排除在制度之外,但是当他带着自己一家人用暴力摧毁了这辆马车,就是在摧毁这个等级制度,就具有了革命的意识——虽然是一种本能:他们抢劫了财物,他们将所谓的贵族脱光了衣服,他甚至让贵妇人委身于他,无疑就是一种颠覆,一种用最简单的暴力完成的颠覆。遇见了爆破专家约翰,胡安和他一起,当初的想法也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但是当这个赤着脚靠着抢劫为生的底层流浪者在武器中升级,在交通工具上升级,甚至从荒野之地坐火车来到了梅萨维多,还要去“遍地是银行”的美国,看起来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钱,但是一种视野的扩大,一些行动的实施,他慢慢成长起来,那就是对于社会的反抗。他目睹了在梅萨维多街上革命者被枪杀的情境,他被约翰带着认识了医生在内“准备自我牺牲”的革命者,他参与了政治监狱150名囚犯的“解放”,他也和约翰一起实施了和政府军作战的行动。胡安的世界里,的确没有所谓的革命,没有政府、土地、国家的概念,“我的国家就是我的家庭。”这是胡安对于革命的定义,没有国只有家,他只希望一家人能够有饭吃有衣穿,当然,抢劫只不过是为了提供基本的保障。当他一家人最终被政府军杀死在洞穴里的时候,他感到的是整个王国的坍塌,而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需要从被动接受命运的人转变为主动改变命运的人,虽然不彻底,但至少可以慢慢觉醒。他和约翰对于革命的对话,其实就代表了两种革命态度,约翰所说的革命是一种和国家、土地、政府、军队相关的宏大叙事,而胡安所说的革命和基本生活有关,和个体命运有关,甚至和等级之间的差别有关:“革命,我可了解是怎么回事,识字的人告诉那些不识字的人,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于是那些不识字穷人就去干,但是无论革命成功与否,到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死的都是那些不识字的穷人,然后再来一遍,而识字的人围坐在大桌边。”这是胡安基于个人经历的愤怒,但其实触及到了革命的本质,那就是反对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如果永远不识字,就永远没有出路。也只有在最底层的胡安能够触及到革命的本质,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一个朝着大路撒尿的人,一个赤着脚打劫的人,当他劫走了马车上富人的财物,当他让女贵妇委身于他,都是他不自觉颠覆这种被阶级固化观念的开始,而约翰带着他抢劫银行,加入组织,参加行动,虽然他的目的还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还是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但是他在耳濡目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初级革命者,释放150名囚犯,向政府军射击,都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实践,而在那列火车上,当约翰给了他枪让他处理执政官时,胡安一只手拿着执政官想要换命而给他的珠宝,另一只手却扣动了扳机,打死了正想逃跑的执政官——左手是珠宝,右手是手枪,左手是财富,右手是暴力,左手是个人的欲望,右手是组织的使命——当胡安用左手和右手完成一次行动,他在双重意义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在释放了囚犯之后,大家把他高高抬起称他是“英雄”,从劫匪到英雄,这是胡安身份的第一次转换,而从英雄到最后被命名为将军,是胡安身份的第二次转换,但是胡安只是一个需要打破自身命运的人,只是想要改变社会现实的人,只是一个具有革命萌芽的人,但是他被命名的身份里——仅仅是命名,还无法成为真正觉醒的革命者,还不能主动拿起武器进行推翻压迫阶级的斗争,当这个时候约翰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离开,实际上革命留下的是一个没有真正完成续承的空挡:实现了私人目的的约翰不是彻底的革命者,在“一把雷管”里成长起来的胡安还没有真正具有成熟的革命意识,于是在两种革命者的断裂中,“革命往事”便也只是变成了充斥着暴力、填满了私欲的行为艺术,爆炸过后,也许是“Duck You Sucker”的惘然和迷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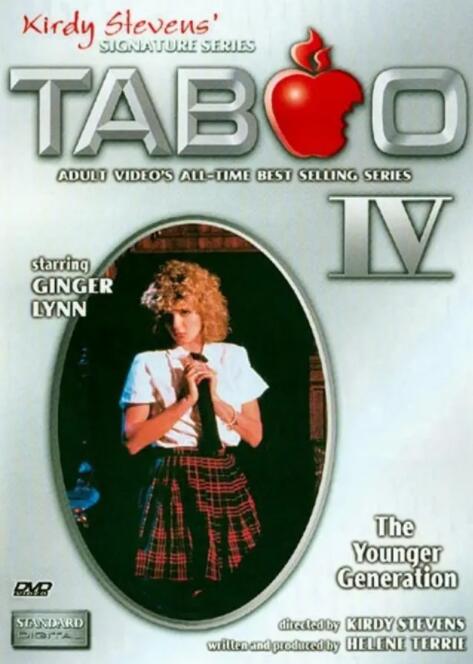



奥先生的故事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