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简介:一个男人在他以前从未回家的时候回到家。灯光从一个奇怪的角度照在他身上,四周都是冰箱的嗡嗡声。一个男人在他以前从未回家的时候回家了。一瞬间,他甚至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房子。正午的这个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寂静和压抑。一个男人突然回到家,看到了一些他被忽视的神秘事物。光从外面进来,天空中漫天的尘土飞扬。妻子在床上安详地睡着了,盖在胸前的设计杂志随着她的呼吸起伏。杂志的价格标签也贴在杂志的封底上。一个男人回到家,看着构成他生活的事物——室外停车场、楼梯和他的信箱,看起来就像一个旅行者。一个人回到家,不经意间出现在他一生中从未到过的地方。他用童年的眼光看着自己,再一次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个充满魔法的藏身之地——那些走廊、通道和锅炉房似乎又充满了魔法,一个人站在旁观他从一个角度观察自己的生活,但他观察的对象还是他自己的生活吗?“我喜欢一回家,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自己和别人的理想打拼。”每每在抗震救灾时期催人泪下响起的励志歌曲,总向人们描述着一种简单的小幸福。虽然三点一线,但足以体现浓浓深情。
人,既安享于流水线般的习惯,又总压抑不住好奇的渴望越界的内心。家庭、交通、上班,努力维系着三者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却总不能避免某些时候在某一头抛下的一个失控砝码,比如,意外归来?
列宾的著名油画《意外归来》里,是一个离家多年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已然陌生甚至成员结构发生变化的家庭中,各种错愕的表情清楚的写在画中人物的脸上;而以色列电影《替代》中的意外归来,则是一个地铁般准点的上班教授某次因忘带文件在午休时分的回家。导演在一开头,就为作为大学物理教授的主人公奥戴德营造着可供后续变化进行比对的日常生活场景:准点起床吃早餐、陆续离开公寓的私家车、下楼坐公交去学校、课堂上每学年都重复一遍的算法公式、午休时在教研室的几声嬉笑、下班回家后电梯间外的同样脸孔、吃饭看电视上床做爱睡觉。有着妻子微笑的脸庞,有着为梦想打拼的男耕女织小幸福。午后回家拿文件像一粒沙子丢入真空状态下的这个平衡日常,清晨拥挤的公交车就只有一个乘客、小区里的停车场空空荡荡、电梯间前没有别人,还有终于激起奥戴德内心涟漪和随后蝴蝶效应的家居静物画:桌上的花瓶在正午最强烈的阳光下盛放、屋尘在丁达尔现象的光斑里跳舞、学习了一上午的爱妻在景深处的卧室小憩。这番寻常不过的景象,却彻底凝住了主人公的注意力,原来他本该是一个对细节极其敏感的生活艺术家,桌上滚动下的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他澎湃。
于是我们这位最讲求线性时序的超理性物理教授,开始以一个文青的姿态重新介入生活发现生活,再说,物理学家往往也就是最能通晓世界气象的诗人哲学家。他找到不去上课的借口,开始在这死气沉沉的建筑里转悠——奥戴德妻子的身份,也是一位极其讲究生活工整的建筑师。接着碰上了略微激荡起他那些许反社会人格一面的邻居约尔夫,从一个好奇的生活细节观察者,成为一个表演非我状态的兴奋演员。两个逃避日常的老男人,在车去室空的停车场躺下晒太阳,在楼道里玩起敲门就抛开的孩童游戏,甚至对着确定主人和狗都不在的屋子怒吼平日说不出的下流句子。
导演艾伦•科勒林,其实是那种非得通过脸谱化角色和风格化造型,才能带出独特趣味的作者,在前作《乐队造访》中,就有着一伙各个古怪的埃及警察乐队,尤其是那个总以为自己是猫王的帅警官,背景设置本身就具文化冲突的张力,加上西部片式的小镇和角色音乐家身份,不产生乐趣都难。可到了这部新作《替代》里,角色的异样就只能设置在板着脸的物理教授身上,导演在建筑空间里表达能激荡内心体验的细节处理能力,显然不够自信(这方面最牛逼的当属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于是得加诸过多脱离常人行为逻辑的场景,在情绪铺垫不足的时候,就将一个规矩的教授变为一个反社会的家伙。
毕竟这不是煽动为独立自我进行革命的cult片,两个楼道里的历险者没有带动所有邻居一道砸电视烧家具。导演或许也觉察到这样的性格变化过于荒谬,于是让教授的妻子也始终安于宁静的微笑日常,在接近尾声的地方,将影片视角从观察和表演生活的教授,调整为好奇丈夫怎么像疯了一样的妻子。
于是,奥戴德不过还是一大堆准点奔波的生活列车中,暂时除了故障的那部,在公寓般生存的人生长河里,激不起一丝涟漪。
人,既安享于流水线般的习惯,又总压抑不住好奇的渴望越界的内心。家庭、交通、上班,努力维系着三者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却总不能避免某些时候在某一头抛下的一个失控砝码,比如,意外归来?
列宾的著名油画《意外归来》里,是一个离家多年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已然陌生甚至成员结构发生变化的家庭中,各种错愕的表情清楚的写在画中人物的脸上;而以色列电影《替代》中的意外归来,则是一个地铁般准点的上班教授某次因忘带文件在午休时分的回家。导演在一开头,就为作为大学物理教授的主人公奥戴德营造着可供后续变化进行比对的日常生活场景:准点起床吃早餐、陆续离开公寓的私家车、下楼坐公交去学校、课堂上每学年都重复一遍的算法公式、午休时在教研室的几声嬉笑、下班回家后电梯间外的同样脸孔、吃饭看电视上床做爱睡觉。有着妻子微笑的脸庞,有着为梦想打拼的男耕女织小幸福。午后回家拿文件像一粒沙子丢入真空状态下的这个平衡日常,清晨拥挤的公交车就只有一个乘客、小区里的停车场空空荡荡、电梯间前没有别人,还有终于激起奥戴德内心涟漪和随后蝴蝶效应的家居静物画:桌上的花瓶在正午最强烈的阳光下盛放、屋尘在丁达尔现象的光斑里跳舞、学习了一上午的爱妻在景深处的卧室小憩。这番寻常不过的景象,却彻底凝住了主人公的注意力,原来他本该是一个对细节极其敏感的生活艺术家,桌上滚动下的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他澎湃。
于是我们这位最讲求线性时序的超理性物理教授,开始以一个文青的姿态重新介入生活发现生活,再说,物理学家往往也就是最能通晓世界气象的诗人哲学家。他找到不去上课的借口,开始在这死气沉沉的建筑里转悠——奥戴德妻子的身份,也是一位极其讲究生活工整的建筑师。接着碰上了略微激荡起他那些许反社会人格一面的邻居约尔夫,从一个好奇的生活细节观察者,成为一个表演非我状态的兴奋演员。两个逃避日常的老男人,在车去室空的停车场躺下晒太阳,在楼道里玩起敲门就抛开的孩童游戏,甚至对着确定主人和狗都不在的屋子怒吼平日说不出的下流句子。
导演艾伦•科勒林,其实是那种非得通过脸谱化角色和风格化造型,才能带出独特趣味的作者,在前作《乐队造访》中,就有着一伙各个古怪的埃及警察乐队,尤其是那个总以为自己是猫王的帅警官,背景设置本身就具文化冲突的张力,加上西部片式的小镇和角色音乐家身份,不产生乐趣都难。可到了这部新作《替代》里,角色的异样就只能设置在板着脸的物理教授身上,导演在建筑空间里表达能激荡内心体验的细节处理能力,显然不够自信(这方面最牛逼的当属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于是得加诸过多脱离常人行为逻辑的场景,在情绪铺垫不足的时候,就将一个规矩的教授变为一个反社会的家伙。
毕竟这不是煽动为独立自我进行革命的cult片,两个楼道里的历险者没有带动所有邻居一道砸电视烧家具。导演或许也觉察到这样的性格变化过于荒谬,于是让教授的妻子也始终安于宁静的微笑日常,在接近尾声的地方,将影片视角从观察和表演生活的教授,调整为好奇丈夫怎么像疯了一样的妻子。
于是,奥戴德不过还是一大堆准点奔波的生活列车中,暂时除了故障的那部,在公寓般生存的人生长河里,激不起一丝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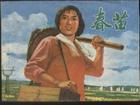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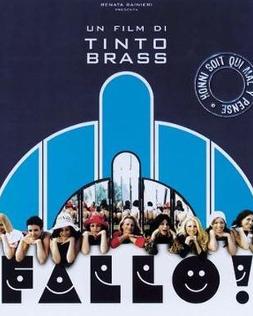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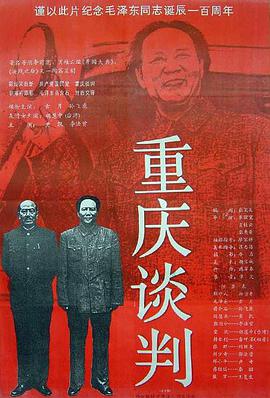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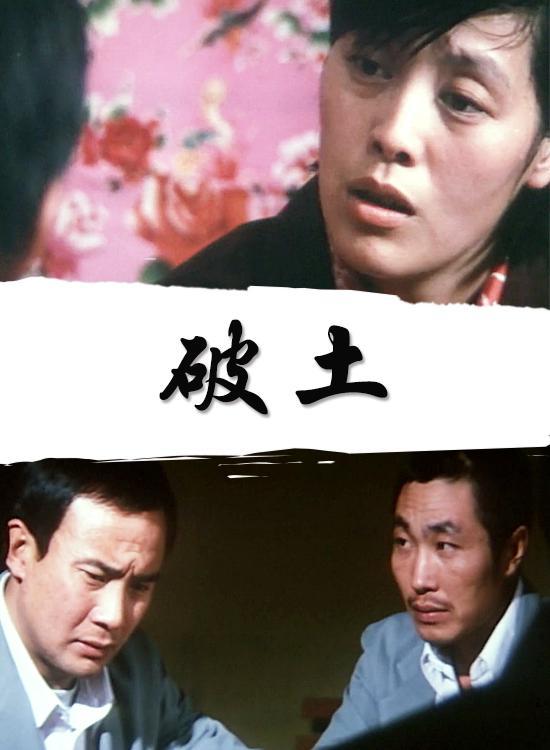

此生当别生(希伯来语)影评
人,既安享于流水线般的习惯,又总压抑不住好奇的渴望越界的内心。家庭、交通、上班,努力维系着三者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却总不能避免某些时候在某一头抛下的一个失控砝码,比如,意外归来?
列宾的著名油画《意外归来》里,是一个离家多年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已然陌生甚至成员结构发生变化的家庭中,各种错愕的表情清楚的写在画中人物的脸上;而以色列电影《替代》中的意外归来,则是一个地铁般准点的上班教授某次因忘带文件在午休时分的回家。导演在一开头,就为作为大学物理教授的主人公奥戴德营造着可供后续变化进行比对的日常生活场景:准点起床吃早餐、陆续离开公寓的私家车、下楼坐公交去学校、课堂上每学年都重复一遍的算法公式、午休时在教研室的几声嬉笑、下班回家后电梯间外的同样脸孔、吃饭看电视上床做爱睡觉。有着妻子微笑的脸庞,有着为梦想打拼的男耕女织小幸福。午后回家拿文件像一粒沙子丢入真空状态下的这个平衡日常,清晨拥挤的公交车就只有一个乘客、小区里的停车场空空荡荡、电梯间前没有别人,还有终于激起奥戴德内心涟漪和随后蝴蝶效应的家居静物画:桌上的花瓶在正午最强烈的阳光下盛放、屋尘在丁达尔现象的光斑里跳舞、学习了一上午的爱妻在景深处的卧室小憩。这番寻常不过的景象,却彻底凝住了主人公的注意力,原来他本该是一个对细节极其敏感的生活艺术家,桌上滚动下的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他澎湃。
于是我们这位最讲求线性时序的超理性物理教授,开始以一个文青的姿态重新介入生活发现生活,再说,物理学家往往也就是最能通晓世界气象的诗人哲学家。他找到不去上课的借口,开始在这死气沉沉的建筑里转悠——奥戴德妻子的身份,也是一位极其讲究生活工整的建筑师。接着碰上了略微激荡起他那些许反社会人格一面的邻居约尔夫,从一个好奇的生活细节观察者,成为一个表演非我状态的兴奋演员。两个逃避日常的老男人,在车去室空的停车场躺下晒太阳,在楼道里玩起敲门就抛开的孩童游戏,甚至对着确定主人和狗都不在的屋子怒吼平日说不出的下流句子。
导演艾伦•科勒林,其实是那种非得通过脸谱化角色和风格化造型,才能带出独特趣味的作者,在前作《乐队造访》中,就有着一伙各个古怪的埃及警察乐队,尤其是那个总以为自己是猫王的帅警官,背景设置本身就具文化冲突的张力,加上西部片式的小镇和角色音乐家身份,不产生乐趣都难。可到了这部新作《替代》里,角色的异样就只能设置在板着脸的物理教授身上,导演在建筑空间里表达能激荡内心体验的细节处理能力,显然不够自信(这方面最牛逼的当属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于是得加诸过多脱离常人行为逻辑的场景,在情绪铺垫不足的时候,就将一个规矩的教授变为一个反社会的家伙。
毕竟这不是煽动为独立自我进行革命的cult片,两个楼道里的历险者没有带动所有邻居一道砸电视烧家具。导演或许也觉察到这样的性格变化过于荒谬,于是让教授的妻子也始终安于宁静的微笑日常,在接近尾声的地方,将影片视角从观察和表演生活的教授,调整为好奇丈夫怎么像疯了一样的妻子。
于是,奥戴德不过还是一大堆准点奔波的生活列车中,暂时除了故障的那部,在公寓般生存的人生长河里,激不起一丝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