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惠特尼(Aump)是一家大公司的唯一女继承人,她从国外留学归来,破坏了她父亲阿莫尼(Amoni)和Kongkaew的婚礼。惠特尼以不回学校的方式抗议这桩婚姻。她开着继母Kongkaew的车去见母亲Maeo.在路上,她驾驶的汽车追尾了一辆……不同于电影还有着商业艺术的划分,电视剧可能圄于其表现形式,它的全部功能就是娱乐大众。因此评价一部电视剧,标准也是单一的:只要是观众爱看、收视率高能赚钱,就该给5星。
《甄嬛传》在国产剧里拍的算是相当认真。比方说:第一集和最后一集,为了象征权力斗争之“周而复始”,皇帝登基的镜头是一模一样的,这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处理方式一样,开头结尾都是老爷纳新妾。还有它有草蛇灰线,线索埋伏比较长,不把观众当傻逼,这一点十分难得。比如,第一集给隆科多、年羹尧封爵后,瓜尔佳鄂敏出宫就去拍“股肱之臣”的马屁,甄远道出门就谁都没搭理;第二集皇上就给华妃娘娘说这欢宜香“只有你有”;华妃第一次见皇后摆完架子走人时,丽嫔也马上告退,还给了曹贵人一个眼色,但曹贵人犹豫了一下没走,而是等了会儿跟着其他妃嫔一起走。这几个梗基本上埋了30多集才露出眉目。类似的铺垫很多,导致看完全剧再看前30集会更有意思,但后40多集就因为只是在揭谜底不太好看了。
《甄嬛传》还展示了后宫斗争的必然性。它不是安排一个二逼(i.e.还珠格格)不知规则、不按规则,却能顺风顺水;反倒是说如果有这种二逼(i.e.淳常在),那她也会稀里糊涂的死在斗争中。齐泽克在《少甚于无》(Less than Nothing)里,提到三种人:二逼(idiot)、傻逼(moron)和苦逼(imbecile)。二逼是那种不知道“大他者”(后宫的规则)存在的人,他们可能智商很高,但不能理解一些基本的社会规则(例如 Sheldon),《甄嬛传》里的淳常在就是这种二逼。傻逼是那种特别依附于“大他者”的,完全将自己认同于意识形态、社会常识的人,比如每一个侦探都需要这样的傻逼:福尔摩斯的华生,波罗的黑斯廷斯,他们代表了“常识”,《甄嬛传》里这种傻逼很多,安陵容可以看做她们的一个代表。而苦逼则是在二逼和傻逼之间:他们认识到了“大他者”的存在和必要性,但并不完全依赖和信任它,齐泽克认为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不断在追问大他者(语言)的可靠性,《甄嬛传》里的苦逼就是甄嬛和沈眉庄。
下面我们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后宫的斗争是必然的?在后宫这个系统中,权力始终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存在的。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是挂灯笼,在《甄嬛传》里是翻牌子。这个权力核心本身又是不在场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老爷几乎从不露面,就象征了这种不在场。《甄嬛传》中雍正虽然常常逗留在后宫,但在许多场合里,他的在场是蹊跷的:雍正在场的情况下,后宫诸妃也在唇枪舌剑,雍正几乎不打断她们的争论,像辩论会的主持人一样只起一个“递话”的作用,这在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可见还是把他处理成了不在场的。这就导致后宫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权力的效果是无所不在的(表现在太监、宫女、其他妃嫔对你的眼神里),但权力本身又是不在场、不固定的,只以翻牌子的形式在各宫流转。同时本来应该保持中立的后宫规则执行人皇后,也是参与者,并没有一个真正可靠中立而且掌握和公开所有信息的机构存在(例如 证券交易委员会)。因此在这样的系统中,当且仅当所有人都选择勾心斗角时,才能达到纳什均衡:给定别的嫔妃选择不勾心斗角,那么你选择勾心斗角是最优选择;给定别的嫔妃选择勾心斗角,那么你还得选择勾心斗角才是最优选择。一个衍生的问题也因此得到了回答:为什么后宫里的各种同盟(例如 华妃党)也都瓦解了?在同盟里,成员们经常要面对“囚徒困境”,个人理性与同盟的集体理性时有冲突:在囚徒困境里,囚犯选择坦白从宽,也就是背叛同伙是最优解。也就是说,华妃党这种卡特尔并不是处在均衡状态。因此甄嬛刚入宫就对宫女太监们说,她不要求别的,就要一个忠诚,即放弃个人理性服从集体理性,使甄嬛的利益最大化。虽说一切集权主义都有这个要求,忠于党和国家,忠于毛主席什么的,但在这个“忠诚化”的过程,即仆人(例如 崔槿汐)的自我意识异化并等同于主人的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被压迫者认同了压迫者的意识形态,被毛主席害死的人死前也真心高呼毛主席万岁),在这过程中也产生了高贵的意识:骑士忠于国王是高贵的,国王忠于上帝是高贵的,崔槿汐忠于甄嬛也是高贵的。在这种本来是最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的权力斗争中,反倒最容易产生崇高感,就像本来是最荒谬的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里却最能表现崇高感一样。
《甄嬛传》还规定了宫斗剧的普遍形式。琼瑶说《甄嬛传》是宫斗剧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内容上虽然未必,但在形式上确实如此。《甄嬛传》里的人物看似各有各的性格,但实际上他们说话的风格高度相似,像“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样本来很个人化的用法,从皇后到宫女到尼姑都时时刻刻在用,这本来是小说的缺点,说明作者没能力根据个人不同的性格写出不同风格的语言来,但在研究宫斗的“形式”时却成了优点,偶然的、特殊的人物性格不是主要因素,而必然的、普遍的结构和形式才是重点。后宫中的人物,主人有:太后、皇后、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仆人有:姑姑、宫女、大太监、小太监、太医。主人限制条件有:出身、位分、长相、年龄、技能、是否有子嗣、与前朝的关系、与其他主子的关系、与奴才的关系;奴才限制条件有:职位、师承、长相、才能、与主子的关系。以后拍宫斗剧要做的,无非是把所有的人物、人物的限制条件做一个排列组合,给人物编排一些性格,再做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再加上能影响整个系统平衡的“黑天鹅事件”(例如 瘟疫和驾崩),就齐活了。在内容上,以后的宫斗剧可以更搞笑、更煽情、更阴谋诡计、更风卷残云、更小人物视角,甚至可以从宫斗剧变成办公室政治、世界大国角力也毫不费劲,但在形式上是已经被《甄嬛传》规定了的。这个普遍形式,就像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规定了剧本形式和镜头风格,就可以派生出在内容上完全不同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这个表现了权力结构的普遍形式是如此有趣,以至于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来计算机模拟这些人物在其中的运动呢?存在主义者当然会反对这一设想,他们问:你把个人偶然的体验置于何地?这就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头,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电视剧“只要赚钱,就给5星”,或为什么《甄嬛传》采取电视剧的形式?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女主角巩俐最后是疯疯癫癫,在《甄嬛传》里,女主角孙俪最后是风风光光。这两种结局,与其说反映了传统男性权力结构下女性所遭遇的不同结局,不如说是在普遍性权力的情况下,个人面对权力做出的不同选择:前一种是拒绝权力的竹林七贤范儿,后一种是认可权力的帝王师style。疯癫与不合作只有在电影的形式下,才可能在商业/艺术的分野下获得认可,个人混乱冲突的体验,也只可能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甄嬛传》作为电视剧,就是要向大他者妥协,就不能以疯疯癫癫、拒绝合作来触怒它(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触怒观众那样),只有承认收视率、赚钱是唯一准则。寺庙/皇宫就是这两种选择的象征,甄嬛最后选择回宫,剧情上是因为得到允礼死讯这一偶然性,实际上是因为全面承认权力:只有权力才能实现她的欲望。因此“娘娘回宫”和“屌丝逆袭”一样,是权力普遍性的胜利,权力的无所不在把“化外之民”重新纳入到它的形式和规则之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已然建立,个人的“诗意”自然无处寻觅。因此,屌丝青年只能是前面定义的苦逼:他不可能无视权力规则,做一个欢乐多的二逼青年;也不愿意成为完全认同权力规则的傻逼青年。在这拧巴的分裂里,苦逼的屌丝青年只能放弃文艺选择逆袭。
《甄嬛传》在国产剧里拍的算是相当认真。比方说:第一集和最后一集,为了象征权力斗争之“周而复始”,皇帝登基的镜头是一模一样的,这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处理方式一样,开头结尾都是老爷纳新妾。还有它有草蛇灰线,线索埋伏比较长,不把观众当傻逼,这一点十分难得。比如,第一集给隆科多、年羹尧封爵后,瓜尔佳鄂敏出宫就去拍“股肱之臣”的马屁,甄远道出门就谁都没搭理;第二集皇上就给华妃娘娘说这欢宜香“只有你有”;华妃第一次见皇后摆完架子走人时,丽嫔也马上告退,还给了曹贵人一个眼色,但曹贵人犹豫了一下没走,而是等了会儿跟着其他妃嫔一起走。这几个梗基本上埋了30多集才露出眉目。类似的铺垫很多,导致看完全剧再看前30集会更有意思,但后40多集就因为只是在揭谜底不太好看了。
《甄嬛传》还展示了后宫斗争的必然性。它不是安排一个二逼(i.e.还珠格格)不知规则、不按规则,却能顺风顺水;反倒是说如果有这种二逼(i.e.淳常在),那她也会稀里糊涂的死在斗争中。齐泽克在《少甚于无》(Less than Nothing)里,提到三种人:二逼(idiot)、傻逼(moron)和苦逼(imbecile)。二逼是那种不知道“大他者”(后宫的规则)存在的人,他们可能智商很高,但不能理解一些基本的社会规则(例如 Sheldon),《甄嬛传》里的淳常在就是这种二逼。傻逼是那种特别依附于“大他者”的,完全将自己认同于意识形态、社会常识的人,比如每一个侦探都需要这样的傻逼:福尔摩斯的华生,波罗的黑斯廷斯,他们代表了“常识”,《甄嬛传》里这种傻逼很多,安陵容可以看做她们的一个代表。而苦逼则是在二逼和傻逼之间:他们认识到了“大他者”的存在和必要性,但并不完全依赖和信任它,齐泽克认为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不断在追问大他者(语言)的可靠性,《甄嬛传》里的苦逼就是甄嬛和沈眉庄。
下面我们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后宫的斗争是必然的?在后宫这个系统中,权力始终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存在的。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是挂灯笼,在《甄嬛传》里是翻牌子。这个权力核心本身又是不在场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老爷几乎从不露面,就象征了这种不在场。《甄嬛传》中雍正虽然常常逗留在后宫,但在许多场合里,他的在场是蹊跷的:雍正在场的情况下,后宫诸妃也在唇枪舌剑,雍正几乎不打断她们的争论,像辩论会的主持人一样只起一个“递话”的作用,这在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可见还是把他处理成了不在场的。这就导致后宫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权力的效果是无所不在的(表现在太监、宫女、其他妃嫔对你的眼神里),但权力本身又是不在场、不固定的,只以翻牌子的形式在各宫流转。同时本来应该保持中立的后宫规则执行人皇后,也是参与者,并没有一个真正可靠中立而且掌握和公开所有信息的机构存在(例如 证券交易委员会)。因此在这样的系统中,当且仅当所有人都选择勾心斗角时,才能达到纳什均衡:给定别的嫔妃选择不勾心斗角,那么你选择勾心斗角是最优选择;给定别的嫔妃选择勾心斗角,那么你还得选择勾心斗角才是最优选择。一个衍生的问题也因此得到了回答:为什么后宫里的各种同盟(例如 华妃党)也都瓦解了?在同盟里,成员们经常要面对“囚徒困境”,个人理性与同盟的集体理性时有冲突:在囚徒困境里,囚犯选择坦白从宽,也就是背叛同伙是最优解。也就是说,华妃党这种卡特尔并不是处在均衡状态。因此甄嬛刚入宫就对宫女太监们说,她不要求别的,就要一个忠诚,即放弃个人理性服从集体理性,使甄嬛的利益最大化。虽说一切集权主义都有这个要求,忠于党和国家,忠于毛主席什么的,但在这个“忠诚化”的过程,即仆人(例如 崔槿汐)的自我意识异化并等同于主人的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被压迫者认同了压迫者的意识形态,被毛主席害死的人死前也真心高呼毛主席万岁),在这过程中也产生了高贵的意识:骑士忠于国王是高贵的,国王忠于上帝是高贵的,崔槿汐忠于甄嬛也是高贵的。在这种本来是最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的权力斗争中,反倒最容易产生崇高感,就像本来是最荒谬的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里却最能表现崇高感一样。
《甄嬛传》还规定了宫斗剧的普遍形式。琼瑶说《甄嬛传》是宫斗剧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内容上虽然未必,但在形式上确实如此。《甄嬛传》里的人物看似各有各的性格,但实际上他们说话的风格高度相似,像“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样本来很个人化的用法,从皇后到宫女到尼姑都时时刻刻在用,这本来是小说的缺点,说明作者没能力根据个人不同的性格写出不同风格的语言来,但在研究宫斗的“形式”时却成了优点,偶然的、特殊的人物性格不是主要因素,而必然的、普遍的结构和形式才是重点。后宫中的人物,主人有:太后、皇后、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仆人有:姑姑、宫女、大太监、小太监、太医。主人限制条件有:出身、位分、长相、年龄、技能、是否有子嗣、与前朝的关系、与其他主子的关系、与奴才的关系;奴才限制条件有:职位、师承、长相、才能、与主子的关系。以后拍宫斗剧要做的,无非是把所有的人物、人物的限制条件做一个排列组合,给人物编排一些性格,再做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再加上能影响整个系统平衡的“黑天鹅事件”(例如 瘟疫和驾崩),就齐活了。在内容上,以后的宫斗剧可以更搞笑、更煽情、更阴谋诡计、更风卷残云、更小人物视角,甚至可以从宫斗剧变成办公室政治、世界大国角力也毫不费劲,但在形式上是已经被《甄嬛传》规定了的。这个普遍形式,就像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规定了剧本形式和镜头风格,就可以派生出在内容上完全不同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这个表现了权力结构的普遍形式是如此有趣,以至于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来计算机模拟这些人物在其中的运动呢?存在主义者当然会反对这一设想,他们问:你把个人偶然的体验置于何地?这就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头,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电视剧“只要赚钱,就给5星”,或为什么《甄嬛传》采取电视剧的形式?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女主角巩俐最后是疯疯癫癫,在《甄嬛传》里,女主角孙俪最后是风风光光。这两种结局,与其说反映了传统男性权力结构下女性所遭遇的不同结局,不如说是在普遍性权力的情况下,个人面对权力做出的不同选择:前一种是拒绝权力的竹林七贤范儿,后一种是认可权力的帝王师style。疯癫与不合作只有在电影的形式下,才可能在商业/艺术的分野下获得认可,个人混乱冲突的体验,也只可能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甄嬛传》作为电视剧,就是要向大他者妥协,就不能以疯疯癫癫、拒绝合作来触怒它(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触怒观众那样),只有承认收视率、赚钱是唯一准则。寺庙/皇宫就是这两种选择的象征,甄嬛最后选择回宫,剧情上是因为得到允礼死讯这一偶然性,实际上是因为全面承认权力:只有权力才能实现她的欲望。因此“娘娘回宫”和“屌丝逆袭”一样,是权力普遍性的胜利,权力的无所不在把“化外之民”重新纳入到它的形式和规则之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已然建立,个人的“诗意”自然无处寻觅。因此,屌丝青年只能是前面定义的苦逼:他不可能无视权力规则,做一个欢乐多的二逼青年;也不愿意成为完全认同权力规则的傻逼青年。在这拧巴的分裂里,苦逼的屌丝青年只能放弃文艺选择逆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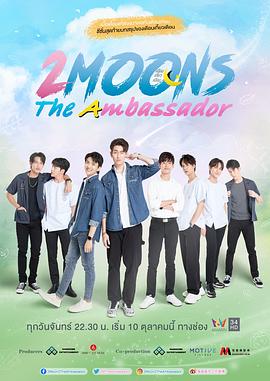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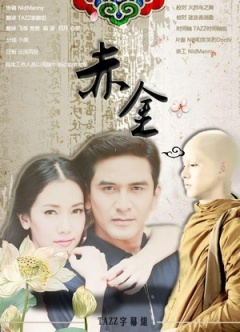




你的爱我无力拒绝影评
《甄嬛传》在国产剧里拍的算是相当认真。比方说:第一集和最后一集,为了象征权力斗争之“周而复始”,皇帝登基的镜头是一模一样的,这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处理方式一样,开头结尾都是老爷纳新妾。还有它有草蛇灰线,线索埋伏比较长,不把观众当傻逼,这一点十分难得。比如,第一集给隆科多、年羹尧封爵后,瓜尔佳鄂敏出宫就去拍“股肱之臣”的马屁,甄远道出门就谁都没搭理;第二集皇上就给华妃娘娘说这欢宜香“只有你有”;华妃第一次见皇后摆完架子走人时,丽嫔也马上告退,还给了曹贵人一个眼色,但曹贵人犹豫了一下没走,而是等了会儿跟着其他妃嫔一起走。这几个梗基本上埋了30多集才露出眉目。类似的铺垫很多,导致看完全剧再看前30集会更有意思,但后40多集就因为只是在揭谜底不太好看了。
《甄嬛传》还展示了后宫斗争的必然性。它不是安排一个二逼(i.e.还珠格格)不知规则、不按规则,却能顺风顺水;反倒是说如果有这种二逼(i.e.淳常在),那她也会稀里糊涂的死在斗争中。齐泽克在《少甚于无》(Less than Nothing)里,提到三种人:二逼(idiot)、傻逼(moron)和苦逼(imbecile)。二逼是那种不知道“大他者”(后宫的规则)存在的人,他们可能智商很高,但不能理解一些基本的社会规则(例如 Sheldon),《甄嬛传》里的淳常在就是这种二逼。傻逼是那种特别依附于“大他者”的,完全将自己认同于意识形态、社会常识的人,比如每一个侦探都需要这样的傻逼:福尔摩斯的华生,波罗的黑斯廷斯,他们代表了“常识”,《甄嬛传》里这种傻逼很多,安陵容可以看做她们的一个代表。而苦逼则是在二逼和傻逼之间:他们认识到了“大他者”的存在和必要性,但并不完全依赖和信任它,齐泽克认为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不断在追问大他者(语言)的可靠性,《甄嬛传》里的苦逼就是甄嬛和沈眉庄。
下面我们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后宫的斗争是必然的?在后宫这个系统中,权力始终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存在的。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是挂灯笼,在《甄嬛传》里是翻牌子。这个权力核心本身又是不在场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老爷几乎从不露面,就象征了这种不在场。《甄嬛传》中雍正虽然常常逗留在后宫,但在许多场合里,他的在场是蹊跷的:雍正在场的情况下,后宫诸妃也在唇枪舌剑,雍正几乎不打断她们的争论,像辩论会的主持人一样只起一个“递话”的作用,这在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可见还是把他处理成了不在场的。这就导致后宫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权力的效果是无所不在的(表现在太监、宫女、其他妃嫔对你的眼神里),但权力本身又是不在场、不固定的,只以翻牌子的形式在各宫流转。同时本来应该保持中立的后宫规则执行人皇后,也是参与者,并没有一个真正可靠中立而且掌握和公开所有信息的机构存在(例如 证券交易委员会)。因此在这样的系统中,当且仅当所有人都选择勾心斗角时,才能达到纳什均衡:给定别的嫔妃选择不勾心斗角,那么你选择勾心斗角是最优选择;给定别的嫔妃选择勾心斗角,那么你还得选择勾心斗角才是最优选择。一个衍生的问题也因此得到了回答:为什么后宫里的各种同盟(例如 华妃党)也都瓦解了?在同盟里,成员们经常要面对“囚徒困境”,个人理性与同盟的集体理性时有冲突:在囚徒困境里,囚犯选择坦白从宽,也就是背叛同伙是最优解。也就是说,华妃党这种卡特尔并不是处在均衡状态。因此甄嬛刚入宫就对宫女太监们说,她不要求别的,就要一个忠诚,即放弃个人理性服从集体理性,使甄嬛的利益最大化。虽说一切集权主义都有这个要求,忠于党和国家,忠于毛主席什么的,但在这个“忠诚化”的过程,即仆人(例如 崔槿汐)的自我意识异化并等同于主人的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被压迫者认同了压迫者的意识形态,被毛主席害死的人死前也真心高呼毛主席万岁),在这过程中也产生了高贵的意识:骑士忠于国王是高贵的,国王忠于上帝是高贵的,崔槿汐忠于甄嬛也是高贵的。在这种本来是最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的权力斗争中,反倒最容易产生崇高感,就像本来是最荒谬的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里却最能表现崇高感一样。
《甄嬛传》还规定了宫斗剧的普遍形式。琼瑶说《甄嬛传》是宫斗剧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内容上虽然未必,但在形式上确实如此。《甄嬛传》里的人物看似各有各的性格,但实际上他们说话的风格高度相似,像“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样本来很个人化的用法,从皇后到宫女到尼姑都时时刻刻在用,这本来是小说的缺点,说明作者没能力根据个人不同的性格写出不同风格的语言来,但在研究宫斗的“形式”时却成了优点,偶然的、特殊的人物性格不是主要因素,而必然的、普遍的结构和形式才是重点。后宫中的人物,主人有:太后、皇后、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仆人有:姑姑、宫女、大太监、小太监、太医。主人限制条件有:出身、位分、长相、年龄、技能、是否有子嗣、与前朝的关系、与其他主子的关系、与奴才的关系;奴才限制条件有:职位、师承、长相、才能、与主子的关系。以后拍宫斗剧要做的,无非是把所有的人物、人物的限制条件做一个排列组合,给人物编排一些性格,再做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再加上能影响整个系统平衡的“黑天鹅事件”(例如 瘟疫和驾崩),就齐活了。在内容上,以后的宫斗剧可以更搞笑、更煽情、更阴谋诡计、更风卷残云、更小人物视角,甚至可以从宫斗剧变成办公室政治、世界大国角力也毫不费劲,但在形式上是已经被《甄嬛传》规定了的。这个普遍形式,就像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规定了剧本形式和镜头风格,就可以派生出在内容上完全不同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这个表现了权力结构的普遍形式是如此有趣,以至于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来计算机模拟这些人物在其中的运动呢?存在主义者当然会反对这一设想,他们问:你把个人偶然的体验置于何地?这就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头,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电视剧“只要赚钱,就给5星”,或为什么《甄嬛传》采取电视剧的形式?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女主角巩俐最后是疯疯癫癫,在《甄嬛传》里,女主角孙俪最后是风风光光。这两种结局,与其说反映了传统男性权力结构下女性所遭遇的不同结局,不如说是在普遍性权力的情况下,个人面对权力做出的不同选择:前一种是拒绝权力的竹林七贤范儿,后一种是认可权力的帝王师style。疯癫与不合作只有在电影的形式下,才可能在商业/艺术的分野下获得认可,个人混乱冲突的体验,也只可能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甄嬛传》作为电视剧,就是要向大他者妥协,就不能以疯疯癫癫、拒绝合作来触怒它(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触怒观众那样),只有承认收视率、赚钱是唯一准则。寺庙/皇宫就是这两种选择的象征,甄嬛最后选择回宫,剧情上是因为得到允礼死讯这一偶然性,实际上是因为全面承认权力:只有权力才能实现她的欲望。因此“娘娘回宫”和“屌丝逆袭”一样,是权力普遍性的胜利,权力的无所不在把“化外之民”重新纳入到它的形式和规则之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已然建立,个人的“诗意”自然无处寻觅。因此,屌丝青年只能是前面定义的苦逼:他不可能无视权力规则,做一个欢乐多的二逼青年;也不愿意成为完全认同权力规则的傻逼青年。在这拧巴的分裂里,苦逼的屌丝青年只能放弃文艺选择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