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5122.html
尤利西斯手上拿着剑,目光朝向前方的大海,当经历了特洛伊战争,当结束十年的海上漂泊,他即将回到自己的国土,即将见到离别的妻子,也即将用剑杀死那些求婚者。这是尤利西斯的回家,当一声“摄像机”“安静”传来的时候,尤利西斯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奥德赛》只不过是一个剧本,在摄像机、剧组人员和导演弗里茨·朗面前,回家的现场只不过是一个片场,但是,当波尔走向平台,向弗里茨·朗伸出手告别的时候,回家却变成了一种互文:“我要回罗马,结束我的剧本,一个人总得结束该结束的东西。”离开,回家,在那一刻,波尔就像尤利西斯一样,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大海在前面,这是荷马史笔下的大海,这是电影《奥德赛》里的大海,这是史诗中的大海,这也是现实中的大海,大海深处真的有一个家?真的有等待自己的妻子?真的有剑光里的杀戮?波尔曾经也面对这一片大海,那时他说:“我们的喜悦马上变成泪水,直到我们靠近大海。”仿佛是一句预言,为什么会有泪水,为什么会在靠近大海时会有泪水?似乎是将《奥德赛》的故事移植到了现实里,尤利西斯在回家之后杀死了那些向妻子珀涅罗珀求婚的求婚者,当夫妻团圆他不应该有悲伤的泪水,但是在这个故事里,争议的地方是:尤利西斯参加特洛伊战争是不是因为无法忍受妻子?或者说,尤利西斯已经觉得妻子不忠了,这是美国制片人普罗可修的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讨论中,弗里茨·朗却认为,不是妻子背叛了尤利西斯,而是她“蔑视”尤利西斯。背叛和蔑视,变成了两种阐述,也正是这相异的解读,使这个剧本走向了两种可能的结局,而对于现实来说,波尔和妻子卡米尔的爱情也在蔑视和背叛中走向那一片流泪的大海。
互文的故事,在摄像机里,也在摄像机外。女人拿着手慢慢地行走,旁边是在轨道上滑行的摄像机,画外音出现,“安德烈巴赞说:电影取代了一个跟我们的愿望更融洽的世界,《蔑视》讲述的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画外音制造的是间离效果,之后摄像机接近镜头,并转向镜头,这一转向很明显的暗示是:镜头对准的是现实,观众可能是演员。这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加上旁白引用巴赞的话来解读《蔑视》,这个多重文本互文的故事就显示出它的层次:电影《奥德赛》构成的是第一层文本,剧组正在这里拍摄根据荷马史诗改变的电影《奥德赛》,围绕着这个电影,美国制片人普罗可修、导演弗里茨·朗、编剧波尔进行过讨论,并力图改编剧本。
在这第一个文本里,就有过大家不用的观点,最主要的是尤利西斯的妻子是否还爱着他,而这也决定了尤利西斯回家的心态,以及杀死求婚者的真正用意。无论是妻子的蔑视还是背叛,最后尤利西斯都拿起了剑,当着最后的结局出现在电影里的时候,引申出了在第二层文本里的讨论,“杀人不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对第一层文本的拒绝,这个结论在第二层文本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波尔和妻子卡米尔回到公寓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坐在浴缸里的卡米尔读到了一本书,书上说:“我们必须反抗,但是杀人不是解决的办法。”第二次提到是在卡米尔和普罗可修乘坐快艇离开拍摄地,波尔和弗里茨·朗讨论尤利西斯的时候,提到他最后拿起剑杀死求婚者不能解决任何办法。
这两次的强调,其实是为第二层文本的结局做一种互文式的铺垫,不管尤利西斯的妻子是蔑视还是不忠,总之,尤利西斯最后杀死了求婚者,而在波尔的故事里,他曾经可能会和尤利西斯一样展开杀戮,因为他出门时带了一把枪,即使那把枪在船上掉了,女助手捡到之后有还给他了,而在他和妻子卡米尔争吵时,从平台走向海湾,直到卡米尔裸体游泳时吗,他身上其实一直带着这把枪,甚至在争吵可能升级的情况下,失去理智的波尔会拿出那把枪,朝向卡米尔,如果再进一步,他还会指向和卡米尔暧昧的普罗可修,那么,波尔就变成了现实中的尤利西斯。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编剧: 让-吕克·戈达尔/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主演: 碧姬·芭铎/米歇尔·皮科利 /杰克·帕兰斯 /更多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 意大利上映日期: 1963-10-29片长: 103分钟又名: 轻蔑 / Contempt
但是,他没有杀人,在主观上或许缺少这一种丧失理智的冲动,和卡米尔发生争执对于波尔来说,更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被蔑视的感觉。而在客观意义上说,他也没有了拿枪杀人的机会,因为在卡米尔游泳之后他靠在岩石上睡着了,仿佛做了一个梦,等他醒来是卡米尔留下的纸条:她把枪里的子弹拿掉了,她和普罗可修离开这里去了罗马,最后是“保重”,是“永别”。他没有能够杀人,他也不会杀人,因为杀人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最后他没有成为尤利西斯——即使他最后和弗里茨·朗告别去罗马,他也没有最终以回家的名义和卡米尔重归于好。
也许在波尔告别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卡米尔其实已经死了,死于一场车祸,当普罗可修和卡米尔开着豪车离开,在加油站加满了油之后,却被一辆槽罐车撞上,双双离世——豪车卡在了卡车的中间,两个人朝着各自的方向死去。一场事故,一次意外,和杀戮无关,和复仇无关,甚至和蔑视无关。所以波尔和卡米尔故事所构筑的第二层文本几乎是在逃离第一层文本,也是在这个逃离意义上,使得“蔑视”这一种情感变得复杂,它无法用杀戮的方式解决,也就是两次强调的那个结论:杀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蔑视》电影海报
复杂的蔑视,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回到波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在前一个晚上,赤身裸体的卡米尔还在问波尔,你是不是爱我整个人?从脚到屁股,从乳房到乳头,从大腿到膝盖,卡米尔躺在床上,一个个地问过去:“你喜欢吗?”而波尔也是一次次地重复:“我喜欢。”这是一个真爱的夜晚,不掺杂任何的外来因素,只有两个人。但是,似乎也有了暗示,当卡米尔赤身裸体的时候,旁边的波尔却穿着衣服,盖着被子,一种肉体被遮蔽的状态,其实和卡米尔开放身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两个人在情爱意义上,是不同步的。
这只是一种暗示,当第二天上午卡米尔去见母亲并陪母亲吃了中饭,而波尔去片场和普罗可修讨论改编剧本的事宜,之后卡米尔也去了那里,也就是从他们重逢在片场之后,两个人的隔阂便出现了。一开始是普罗可修邀请大家去吃饭,车子似乎不能做太多的人,波尔提议卡米尔坐上车,然后自己坐出租车,而女助手则骑自行车。三种交通方式,又是一种相异的隐喻,提前到来的卡米尔在等待了半个小时后才看见波尔抵达,她问为什么这么迟,波尔说没有及时看到出租车,之后又遇到了车祸,但是卡米尔显然已经开始不高兴了,而且显示在了脸上。镜头闪现了刚上车时的情景,这是卡米尔内心活动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她开始滋生了所谓“蔑视”的情绪。
波尔说要去上厕所,卡米尔却看到他和女助手在说话,并有某种暧昧的动作;回到公寓后,卡米尔便告诉他不想去卡普里岛的片场,波尔想不明白原因;之后卡米尔的母亲打电话来,波尔接电话却说卡米尔出去了,听到对话的卡米尔为波尔的撒谎而生气,而波尔只是想测试中午是不是真的和母亲在一起……卡米尔的情绪变化是明显的,所以波尔几次问她怎么回事,是不是刚才发生了什么,卡米尔一直回避正面回答,在两个人的公寓里,事件渐渐升级,一开始是观点不同,后来是争执,最后卡米尔对他说:“我蔑视你,这就是我的感觉。”这是第一次提到“蔑视”,对于波尔来说,问题是,昨晚还好好的,早上出门还好好的,为什么去了片场之后,为什么遇见了普罗可修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卡米尔说到“蔑视”,似乎是一种不屑,一种鄙夷,是自上而下的俯视,那么,从“你爱我整个人”到“蔑视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波尔找到普罗可修这位美国制片人,在同意改编剧本的情况下普罗可修向他开除了一张支票,那么蔑视的一种解读是关于钱。在波尔和卡米尔争吵的时候,也说到了钱,卡米尔说,以前写侦探小说,钱不多,但生活并不坏。但是在和电影制片人认识之后,似乎情况发生了改变,波尔一直解释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为了买下公寓,是为了卡米尔,所以这是一种分歧;在这一天,卡米尔似乎看到了波尔的暧昧举动,听到了他的谎言,是不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以前发生过,这是对于情感的一种背叛,也就是说,那晚被遮掩的身体有了一个解读的理由,而这也是卡米尔产生蔑视的原因;第三重分歧大约是对于爱的理解,卡米尔需要的是彻底的,纯粹的爱,但是无论是公寓还是创作,波尔的爱其实已经建立在物质意义上,甚至卡米尔也成为物质之一,在内心一段心理活动中,波尔说:“如果她死了,我也就失去了我的爱。”而这正是他对“杀人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解,而卡米尔的内心想法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死在他怀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卡米尔看来,这种蔑视一开始只是一种情绪的表露,甚至自己也不甚清楚蔑视是不是意味着不爱,即使当两个人开始有了争吵,卡米尔说了一句:“我不爱你了,没什么可解释的,一切结束了”也并非是真正彻底地变成了仇恨,之后一起在卡普里岛,种种不愉快,种种隔阂之后,卡米尔在那个被太阳照见的平台上,面对着波尔依然裸着身体,像那一晚面对波尔时一样;在海湾处,卡米尔也是脱光了衣服,在波尔在场的情况下裸身入海。
蔑视,只是蔑视,但是蔑视的可怕是冷漠,是隔阂,是分歧,最后甚至真的是仇恨。那一句的“保重”和“永别”,是卡米尔写给波尔的留言,但是在她走向普罗可修的过程中,也并没有真正像尤利西斯的妻子一样,被认为是不忠,戴着墨镜,语言不通,就是她和普罗可修之间无法真正在一起的隐喻,而最后死于车祸,则是一种分离的状态。但是,无论是卡米尔的蔑视还是最后的死亡,似乎都和普罗可修有关,也就是这个被贴上“美国制片人”标签的人,引向了第三层文本。
电影《奥德赛》在拍摄,波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发生在摄像机前,而当镜头前出现摄像机,就代表着《蔑视》之外还有一层文本,那就是这个名为《蔑视》的电影之外的现实,波尔为什么要接手改编剧本的活,大约是钱不够用,而他改编剧本一定是为普罗可修服务的,也就是说,波尔代表的意大利或者欧洲电影,而普罗可修代表的是美国资本,这就是电影时代的一个隐喻:在资本之下,电影该何去何从?代表美国资本的普罗可修其实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所以波尔在和弗里茨对话是说他是“独裁者”,而弗里茨说,就像尤利西斯,是简单、聪明和强壮的男人,所以卡米尔代表的纯粹对波尔的蔑视,其实是艺术电影对好莱坞商业模式的蔑视,而最后波尔终于决定回到罗马结束剧本的改编,像是一次在创作意义上的“回家”,但是卡米尔却被一种客观发生的车祸夺去生命的时候,蔑视是不是也代表着一种无法找到出路的迷惘?
那晚他们躺在床上“爱我的整个人”的时候,光线的滤镜分别是红色和蓝色,以及最后的自然光,似乎就是对法国和美国国旗颜色的一种隐喻,电影在这样的镜像中,到底是走向好莱坞式的商业电影,还是继续坚持回家式的艺术电影?其实答案或者是显露在第三层文本里,为什么戈达尔要把摄像机对准观众?为什么要产生间离效果,因为他要制造的是摄像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好莱坞的梦境构筑是隐藏摄像机,而让摄像机对准摄像机,把摄像机带向剧情,甚至把《蔑视》直接放在电影里成为其中一个文本,就是为了像卡米尔一样显露出每一个值得爱的地方,袒露无疑,才是真实,才是纯粹,而这也是对于好莱坞,对于金钱,对于“谎言市场”的一次真正“蔑视”。
尤利西斯手上拿着剑,目光朝向前方的大海,当经历了特洛伊战争,当结束十年的海上漂泊,他即将回到自己的国土,即将见到离别的妻子,也即将用剑杀死那些求婚者。这是尤利西斯的回家,当一声“摄像机”“安静”传来的时候,尤利西斯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奥德赛》只不过是一个剧本,在摄像机、剧组人员和导演弗里茨·朗面前,回家的现场只不过是一个片场,但是,当波尔走向平台,向弗里茨·朗伸出手告别的时候,回家却变成了一种互文:“我要回罗马,结束我的剧本,一个人总得结束该结束的东西。”离开,回家,在那一刻,波尔就像尤利西斯一样,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大海在前面,这是荷马史笔下的大海,这是电影《奥德赛》里的大海,这是史诗中的大海,这也是现实中的大海,大海深处真的有一个家?真的有等待自己的妻子?真的有剑光里的杀戮?波尔曾经也面对这一片大海,那时他说:“我们的喜悦马上变成泪水,直到我们靠近大海。”仿佛是一句预言,为什么会有泪水,为什么会在靠近大海时会有泪水?似乎是将《奥德赛》的故事移植到了现实里,尤利西斯在回家之后杀死了那些向妻子珀涅罗珀求婚的求婚者,当夫妻团圆他不应该有悲伤的泪水,但是在这个故事里,争议的地方是:尤利西斯参加特洛伊战争是不是因为无法忍受妻子?或者说,尤利西斯已经觉得妻子不忠了,这是美国制片人普罗可修的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讨论中,弗里茨·朗却认为,不是妻子背叛了尤利西斯,而是她“蔑视”尤利西斯。背叛和蔑视,变成了两种阐述,也正是这相异的解读,使这个剧本走向了两种可能的结局,而对于现实来说,波尔和妻子卡米尔的爱情也在蔑视和背叛中走向那一片流泪的大海。
互文的故事,在摄像机里,也在摄像机外。女人拿着手慢慢地行走,旁边是在轨道上滑行的摄像机,画外音出现,“安德烈巴赞说:电影取代了一个跟我们的愿望更融洽的世界,《蔑视》讲述的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画外音制造的是间离效果,之后摄像机接近镜头,并转向镜头,这一转向很明显的暗示是:镜头对准的是现实,观众可能是演员。这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加上旁白引用巴赞的话来解读《蔑视》,这个多重文本互文的故事就显示出它的层次:电影《奥德赛》构成的是第一层文本,剧组正在这里拍摄根据荷马史诗改变的电影《奥德赛》,围绕着这个电影,美国制片人普罗可修、导演弗里茨·朗、编剧波尔进行过讨论,并力图改编剧本。
在这第一个文本里,就有过大家不用的观点,最主要的是尤利西斯的妻子是否还爱着他,而这也决定了尤利西斯回家的心态,以及杀死求婚者的真正用意。无论是妻子的蔑视还是背叛,最后尤利西斯都拿起了剑,当着最后的结局出现在电影里的时候,引申出了在第二层文本里的讨论,“杀人不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对第一层文本的拒绝,这个结论在第二层文本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波尔和妻子卡米尔回到公寓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坐在浴缸里的卡米尔读到了一本书,书上说:“我们必须反抗,但是杀人不是解决的办法。”第二次提到是在卡米尔和普罗可修乘坐快艇离开拍摄地,波尔和弗里茨·朗讨论尤利西斯的时候,提到他最后拿起剑杀死求婚者不能解决任何办法。
这两次的强调,其实是为第二层文本的结局做一种互文式的铺垫,不管尤利西斯的妻子是蔑视还是不忠,总之,尤利西斯最后杀死了求婚者,而在波尔的故事里,他曾经可能会和尤利西斯一样展开杀戮,因为他出门时带了一把枪,即使那把枪在船上掉了,女助手捡到之后有还给他了,而在他和妻子卡米尔争吵时,从平台走向海湾,直到卡米尔裸体游泳时吗,他身上其实一直带着这把枪,甚至在争吵可能升级的情况下,失去理智的波尔会拿出那把枪,朝向卡米尔,如果再进一步,他还会指向和卡米尔暧昧的普罗可修,那么,波尔就变成了现实中的尤利西斯。
但是,他没有杀人,在主观上或许缺少这一种丧失理智的冲动,和卡米尔发生争执对于波尔来说,更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被蔑视的感觉。而在客观意义上说,他也没有了拿枪杀人的机会,因为在卡米尔游泳之后他靠在岩石上睡着了,仿佛做了一个梦,等他醒来是卡米尔留下的纸条:她把枪里的子弹拿掉了,她和普罗可修离开这里去了罗马,最后是“保重”,是“永别”。他没有能够杀人,他也不会杀人,因为杀人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最后他没有成为尤利西斯——即使他最后和弗里茨·朗告别去罗马,他也没有最终以回家的名义和卡米尔重归于好。
也许在波尔告别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卡米尔其实已经死了,死于一场车祸,当普罗可修和卡米尔开着豪车离开,在加油站加满了油之后,却被一辆槽罐车撞上,双双离世——豪车卡在了卡车的中间,两个人朝着各自的方向死去。一场事故,一次意外,和杀戮无关,和复仇无关,甚至和蔑视无关。所以波尔和卡米尔故事所构筑的第二层文本几乎是在逃离第一层文本,也是在这个逃离意义上,使得“蔑视”这一种情感变得复杂,它无法用杀戮的方式解决,也就是两次强调的那个结论:杀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复杂的蔑视,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回到波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在前一个晚上,赤身裸体的卡米尔还在问波尔,你是不是爱我整个人?从脚到屁股,从乳房到乳头,从大腿到膝盖,卡米尔躺在床上,一个个地问过去:“你喜欢吗?”而波尔也是一次次地重复:“我喜欢。”这是一个真爱的夜晚,不掺杂任何的外来因素,只有两个人。但是,似乎也有了暗示,当卡米尔赤身裸体的时候,旁边的波尔却穿着衣服,盖着被子,一种肉体被遮蔽的状态,其实和卡米尔开放身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两个人在情爱意义上,是不同步的。
这只是一种暗示,当第二天上午卡米尔去见母亲并陪母亲吃了中饭,而波尔去片场和普罗可修讨论改编剧本的事宜,之后卡米尔也去了那里,也就是从他们重逢在片场之后,两个人的隔阂便出现了。一开始是普罗可修邀请大家去吃饭,车子似乎不能做太多的人,波尔提议卡米尔坐上车,然后自己坐出租车,而女助手则骑自行车。三种交通方式,又是一种相异的隐喻,提前到来的卡米尔在等待了半个小时后才看见波尔抵达,她问为什么这么迟,波尔说没有及时看到出租车,之后又遇到了车祸,但是卡米尔显然已经开始不高兴了,而且显示在了脸上。镜头闪现了刚上车时的情景,这是卡米尔内心活动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她开始滋生了所谓“蔑视”的情绪。
波尔说要去上厕所,卡米尔却看到他和女助手在说话,并有某种暧昧的动作;回到公寓后,卡米尔便告诉他不想去卡普里岛的片场,波尔想不明白原因;之后卡米尔的母亲打电话来,波尔接电话却说卡米尔出去了,听到对话的卡米尔为波尔的撒谎而生气,而波尔只是想测试中午是不是真的和母亲在一起……卡米尔的情绪变化是明显的,所以波尔几次问她怎么回事,是不是刚才发生了什么,卡米尔一直回避正面回答,在两个人的公寓里,事件渐渐升级,一开始是观点不同,后来是争执,最后卡米尔对他说:“我蔑视你,这就是我的感觉。”这是第一次提到“蔑视”,对于波尔来说,问题是,昨晚还好好的,早上出门还好好的,为什么去了片场之后,为什么遇见了普罗可修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卡米尔说到“蔑视”,似乎是一种不屑,一种鄙夷,是自上而下的俯视,那么,从“你爱我整个人”到“蔑视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波尔找到普罗可修这位美国制片人,在同意改编剧本的情况下普罗可修向他开除了一张支票,那么蔑视的一种解读是关于钱。在波尔和卡米尔争吵的时候,也说到了钱,卡米尔说,以前写侦探小说,钱不多,但生活并不坏。但是在和电影制片人认识之后,似乎情况发生了改变,波尔一直解释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为了买下公寓,是为了卡米尔,所以这是一种分歧;在这一天,卡米尔似乎看到了波尔的暧昧举动,听到了他的谎言,是不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以前发生过,这是对于情感的一种背叛,也就是说,那晚被遮掩的身体有了一个解读的理由,而这也是卡米尔产生蔑视的原因;第三重分歧大约是对于爱的理解,卡米尔需要的是彻底的,纯粹的爱,但是无论是公寓还是创作,波尔的爱其实已经建立在物质意义上,甚至卡米尔也成为物质之一,在内心一段心理活动中,波尔说:“如果她死了,我也就失去了我的爱。”而这正是他对“杀人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解,而卡米尔的内心想法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死在他怀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卡米尔看来,这种蔑视一开始只是一种情绪的表露,甚至自己也不甚清楚蔑视是不是意味着不爱,即使当两个人开始有了争吵,卡米尔说了一句:“我不爱你了,没什么可解释的,一切结束了”也并非是真正彻底地变成了仇恨,之后一起在卡普里岛,种种不愉快,种种隔阂之后,卡米尔在那个被太阳照见的平台上,面对着波尔依然裸着身体,像那一晚面对波尔时一样;在海湾处,卡米尔也是脱光了衣服,在波尔在场的情况下裸身入海。
蔑视,只是蔑视,但是蔑视的可怕是冷漠,是隔阂,是分歧,最后甚至真的是仇恨。那一句的“保重”和“永别”,是卡米尔写给波尔的留言,但是在她走向普罗可修的过程中,也并没有真正像尤利西斯的妻子一样,被认为是不忠,戴着墨镜,语言不通,就是她和普罗可修之间无法真正在一起的隐喻,而最后死于车祸,则是一种分离的状态。但是,无论是卡米尔的蔑视还是最后的死亡,似乎都和普罗可修有关,也就是这个被贴上“美国制片人”标签的人,引向了第三层文本。
电影《奥德赛》在拍摄,波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发生在摄像机前,而当镜头前出现摄像机,就代表着《蔑视》之外还有一层文本,那就是这个名为《蔑视》的电影之外的现实,波尔为什么要接手改编剧本的活,大约是钱不够用,而他改编剧本一定是为普罗可修服务的,也就是说,波尔代表的意大利或者欧洲电影,而普罗可修代表的是美国资本,这就是电影时代的一个隐喻:在资本之下,电影该何去何从?代表美国资本的普罗可修其实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所以波尔在和弗里茨对话是说他是“独裁者”,而弗里茨说,就像尤利西斯,是简单、聪明和强壮的男人,所以卡米尔代表的纯粹对波尔的蔑视,其实是艺术电影对好莱坞商业模式的蔑视,而最后波尔终于决定回到罗马结束剧本的改编,像是一次在创作意义上的“回家”,但是卡米尔却被一种客观发生的车祸夺去生命的时候,蔑视是不是也代表着一种无法找到出路的迷惘?
那晚他们躺在床上“爱我的整个人”的时候,光线的滤镜分别是红色和蓝色,以及最后的自然光,似乎就是对法国和美国国旗颜色的一种隐喻,电影在这样的镜像中,到底是走向好莱坞式的商业电影,还是继续坚持回家式的艺术电影?其实答案或者是显露在第三层文本里,为什么戈达尔要把摄像机对准观众?为什么要产生间离效果,因为他要制造的是摄像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好莱坞的梦境构筑是隐藏摄像机,而让摄像机对准摄像机,把摄像机带向剧情,甚至把《蔑视》直接放在电影里成为其中一个文本,就是为了像卡米尔一样显露出每一个值得爱的地方,袒露无疑,才是真实,才是纯粹,而这也是对于好莱坞,对于金钱,对于“谎言市场”的一次真正“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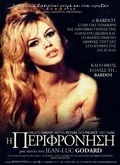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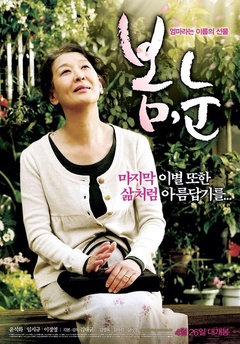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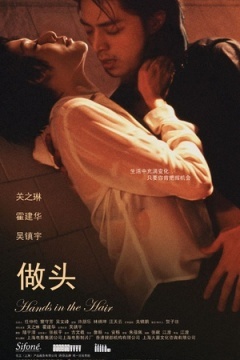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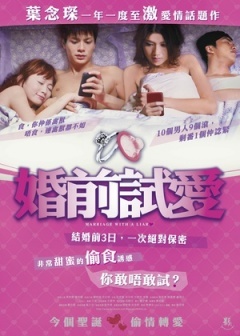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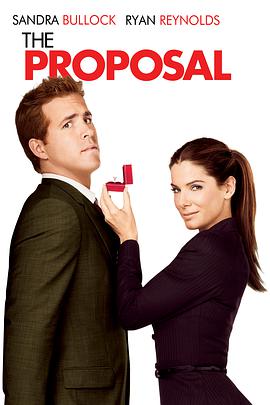
蔑视1963影评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5122.html
尤利西斯手上拿着剑,目光朝向前方的大海,当经历了特洛伊战争,当结束十年的海上漂泊,他即将回到自己的国土,即将见到离别的妻子,也即将用剑杀死那些求婚者。这是尤利西斯的回家,当一声“摄像机”“安静”传来的时候,尤利西斯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奥德赛》只不过是一个剧本,在摄像机、剧组人员和导演弗里茨·朗面前,回家的现场只不过是一个片场,但是,当波尔走向平台,向弗里茨·朗伸出手告别的时候,回家却变成了一种互文:“我要回罗马,结束我的剧本,一个人总得结束该结束的东西。”离开,回家,在那一刻,波尔就像尤利西斯一样,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大海在前面,这是荷马史笔下的大海,这是电影《奥德赛》里的大海,这是史诗中的大海,这也是现实中的大海,大海深处真的有一个家?真的有等待自己的妻子?真的有剑光里的杀戮?波尔曾经也面对这一片大海,那时他说:“我们的喜悦马上变成泪水,直到我们靠近大海。”仿佛是一句预言,为什么会有泪水,为什么会在靠近大海时会有泪水?似乎是将《奥德赛》的故事移植到了现实里,尤利西斯在回家之后杀死了那些向妻子珀涅罗珀求婚的求婚者,当夫妻团圆他不应该有悲伤的泪水,但是在这个故事里,争议的地方是:尤利西斯参加特洛伊战争是不是因为无法忍受妻子?或者说,尤利西斯已经觉得妻子不忠了,这是美国制片人普罗可修的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讨论中,弗里茨·朗却认为,不是妻子背叛了尤利西斯,而是她“蔑视”尤利西斯。背叛和蔑视,变成了两种阐述,也正是这相异的解读,使这个剧本走向了两种可能的结局,而对于现实来说,波尔和妻子卡米尔的爱情也在蔑视和背叛中走向那一片流泪的大海。
互文的故事,在摄像机里,也在摄像机外。女人拿着手慢慢地行走,旁边是在轨道上滑行的摄像机,画外音出现,“安德烈巴赞说:电影取代了一个跟我们的愿望更融洽的世界,《蔑视》讲述的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画外音制造的是间离效果,之后摄像机接近镜头,并转向镜头,这一转向很明显的暗示是:镜头对准的是现实,观众可能是演员。这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加上旁白引用巴赞的话来解读《蔑视》,这个多重文本互文的故事就显示出它的层次:电影《奥德赛》构成的是第一层文本,剧组正在这里拍摄根据荷马史诗改变的电影《奥德赛》,围绕着这个电影,美国制片人普罗可修、导演弗里茨·朗、编剧波尔进行过讨论,并力图改编剧本。
在这第一个文本里,就有过大家不用的观点,最主要的是尤利西斯的妻子是否还爱着他,而这也决定了尤利西斯回家的心态,以及杀死求婚者的真正用意。无论是妻子的蔑视还是背叛,最后尤利西斯都拿起了剑,当着最后的结局出现在电影里的时候,引申出了在第二层文本里的讨论,“杀人不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对第一层文本的拒绝,这个结论在第二层文本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波尔和妻子卡米尔回到公寓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坐在浴缸里的卡米尔读到了一本书,书上说:“我们必须反抗,但是杀人不是解决的办法。”第二次提到是在卡米尔和普罗可修乘坐快艇离开拍摄地,波尔和弗里茨·朗讨论尤利西斯的时候,提到他最后拿起剑杀死求婚者不能解决任何办法。
这两次的强调,其实是为第二层文本的结局做一种互文式的铺垫,不管尤利西斯的妻子是蔑视还是不忠,总之,尤利西斯最后杀死了求婚者,而在波尔的故事里,他曾经可能会和尤利西斯一样展开杀戮,因为他出门时带了一把枪,即使那把枪在船上掉了,女助手捡到之后有还给他了,而在他和妻子卡米尔争吵时,从平台走向海湾,直到卡米尔裸体游泳时吗,他身上其实一直带着这把枪,甚至在争吵可能升级的情况下,失去理智的波尔会拿出那把枪,朝向卡米尔,如果再进一步,他还会指向和卡米尔暧昧的普罗可修,那么,波尔就变成了现实中的尤利西斯。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编剧: 让-吕克·戈达尔/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主演: 碧姬·芭铎/米歇尔·皮科利 /杰克·帕兰斯 /更多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 意大利上映日期: 1963-10-29片长: 103分钟又名: 轻蔑 / Contempt
但是,他没有杀人,在主观上或许缺少这一种丧失理智的冲动,和卡米尔发生争执对于波尔来说,更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被蔑视的感觉。而在客观意义上说,他也没有了拿枪杀人的机会,因为在卡米尔游泳之后他靠在岩石上睡着了,仿佛做了一个梦,等他醒来是卡米尔留下的纸条:她把枪里的子弹拿掉了,她和普罗可修离开这里去了罗马,最后是“保重”,是“永别”。他没有能够杀人,他也不会杀人,因为杀人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最后他没有成为尤利西斯——即使他最后和弗里茨·朗告别去罗马,他也没有最终以回家的名义和卡米尔重归于好。
也许在波尔告别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卡米尔其实已经死了,死于一场车祸,当普罗可修和卡米尔开着豪车离开,在加油站加满了油之后,却被一辆槽罐车撞上,双双离世——豪车卡在了卡车的中间,两个人朝着各自的方向死去。一场事故,一次意外,和杀戮无关,和复仇无关,甚至和蔑视无关。所以波尔和卡米尔故事所构筑的第二层文本几乎是在逃离第一层文本,也是在这个逃离意义上,使得“蔑视”这一种情感变得复杂,它无法用杀戮的方式解决,也就是两次强调的那个结论:杀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蔑视》电影海报
复杂的蔑视,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回到波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在前一个晚上,赤身裸体的卡米尔还在问波尔,你是不是爱我整个人?从脚到屁股,从乳房到乳头,从大腿到膝盖,卡米尔躺在床上,一个个地问过去:“你喜欢吗?”而波尔也是一次次地重复:“我喜欢。”这是一个真爱的夜晚,不掺杂任何的外来因素,只有两个人。但是,似乎也有了暗示,当卡米尔赤身裸体的时候,旁边的波尔却穿着衣服,盖着被子,一种肉体被遮蔽的状态,其实和卡米尔开放身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两个人在情爱意义上,是不同步的。
这只是一种暗示,当第二天上午卡米尔去见母亲并陪母亲吃了中饭,而波尔去片场和普罗可修讨论改编剧本的事宜,之后卡米尔也去了那里,也就是从他们重逢在片场之后,两个人的隔阂便出现了。一开始是普罗可修邀请大家去吃饭,车子似乎不能做太多的人,波尔提议卡米尔坐上车,然后自己坐出租车,而女助手则骑自行车。三种交通方式,又是一种相异的隐喻,提前到来的卡米尔在等待了半个小时后才看见波尔抵达,她问为什么这么迟,波尔说没有及时看到出租车,之后又遇到了车祸,但是卡米尔显然已经开始不高兴了,而且显示在了脸上。镜头闪现了刚上车时的情景,这是卡米尔内心活动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她开始滋生了所谓“蔑视”的情绪。
波尔说要去上厕所,卡米尔却看到他和女助手在说话,并有某种暧昧的动作;回到公寓后,卡米尔便告诉他不想去卡普里岛的片场,波尔想不明白原因;之后卡米尔的母亲打电话来,波尔接电话却说卡米尔出去了,听到对话的卡米尔为波尔的撒谎而生气,而波尔只是想测试中午是不是真的和母亲在一起……卡米尔的情绪变化是明显的,所以波尔几次问她怎么回事,是不是刚才发生了什么,卡米尔一直回避正面回答,在两个人的公寓里,事件渐渐升级,一开始是观点不同,后来是争执,最后卡米尔对他说:“我蔑视你,这就是我的感觉。”这是第一次提到“蔑视”,对于波尔来说,问题是,昨晚还好好的,早上出门还好好的,为什么去了片场之后,为什么遇见了普罗可修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卡米尔说到“蔑视”,似乎是一种不屑,一种鄙夷,是自上而下的俯视,那么,从“你爱我整个人”到“蔑视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波尔找到普罗可修这位美国制片人,在同意改编剧本的情况下普罗可修向他开除了一张支票,那么蔑视的一种解读是关于钱。在波尔和卡米尔争吵的时候,也说到了钱,卡米尔说,以前写侦探小说,钱不多,但生活并不坏。但是在和电影制片人认识之后,似乎情况发生了改变,波尔一直解释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为了买下公寓,是为了卡米尔,所以这是一种分歧;在这一天,卡米尔似乎看到了波尔的暧昧举动,听到了他的谎言,是不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以前发生过,这是对于情感的一种背叛,也就是说,那晚被遮掩的身体有了一个解读的理由,而这也是卡米尔产生蔑视的原因;第三重分歧大约是对于爱的理解,卡米尔需要的是彻底的,纯粹的爱,但是无论是公寓还是创作,波尔的爱其实已经建立在物质意义上,甚至卡米尔也成为物质之一,在内心一段心理活动中,波尔说:“如果她死了,我也就失去了我的爱。”而这正是他对“杀人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解,而卡米尔的内心想法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死在他怀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卡米尔看来,这种蔑视一开始只是一种情绪的表露,甚至自己也不甚清楚蔑视是不是意味着不爱,即使当两个人开始有了争吵,卡米尔说了一句:“我不爱你了,没什么可解释的,一切结束了”也并非是真正彻底地变成了仇恨,之后一起在卡普里岛,种种不愉快,种种隔阂之后,卡米尔在那个被太阳照见的平台上,面对着波尔依然裸着身体,像那一晚面对波尔时一样;在海湾处,卡米尔也是脱光了衣服,在波尔在场的情况下裸身入海。
蔑视,只是蔑视,但是蔑视的可怕是冷漠,是隔阂,是分歧,最后甚至真的是仇恨。那一句的“保重”和“永别”,是卡米尔写给波尔的留言,但是在她走向普罗可修的过程中,也并没有真正像尤利西斯的妻子一样,被认为是不忠,戴着墨镜,语言不通,就是她和普罗可修之间无法真正在一起的隐喻,而最后死于车祸,则是一种分离的状态。但是,无论是卡米尔的蔑视还是最后的死亡,似乎都和普罗可修有关,也就是这个被贴上“美国制片人”标签的人,引向了第三层文本。
电影《奥德赛》在拍摄,波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发生在摄像机前,而当镜头前出现摄像机,就代表着《蔑视》之外还有一层文本,那就是这个名为《蔑视》的电影之外的现实,波尔为什么要接手改编剧本的活,大约是钱不够用,而他改编剧本一定是为普罗可修服务的,也就是说,波尔代表的意大利或者欧洲电影,而普罗可修代表的是美国资本,这就是电影时代的一个隐喻:在资本之下,电影该何去何从?代表美国资本的普罗可修其实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所以波尔在和弗里茨对话是说他是“独裁者”,而弗里茨说,就像尤利西斯,是简单、聪明和强壮的男人,所以卡米尔代表的纯粹对波尔的蔑视,其实是艺术电影对好莱坞商业模式的蔑视,而最后波尔终于决定回到罗马结束剧本的改编,像是一次在创作意义上的“回家”,但是卡米尔却被一种客观发生的车祸夺去生命的时候,蔑视是不是也代表着一种无法找到出路的迷惘?
那晚他们躺在床上“爱我的整个人”的时候,光线的滤镜分别是红色和蓝色,以及最后的自然光,似乎就是对法国和美国国旗颜色的一种隐喻,电影在这样的镜像中,到底是走向好莱坞式的商业电影,还是继续坚持回家式的艺术电影?其实答案或者是显露在第三层文本里,为什么戈达尔要把摄像机对准观众?为什么要产生间离效果,因为他要制造的是摄像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好莱坞的梦境构筑是隐藏摄像机,而让摄像机对准摄像机,把摄像机带向剧情,甚至把《蔑视》直接放在电影里成为其中一个文本,就是为了像卡米尔一样显露出每一个值得爱的地方,袒露无疑,才是真实,才是纯粹,而这也是对于好莱坞,对于金钱,对于“谎言市场”的一次真正“蔑视”。
尤利西斯手上拿着剑,目光朝向前方的大海,当经历了特洛伊战争,当结束十年的海上漂泊,他即将回到自己的国土,即将见到离别的妻子,也即将用剑杀死那些求婚者。这是尤利西斯的回家,当一声“摄像机”“安静”传来的时候,尤利西斯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奥德赛》只不过是一个剧本,在摄像机、剧组人员和导演弗里茨·朗面前,回家的现场只不过是一个片场,但是,当波尔走向平台,向弗里茨·朗伸出手告别的时候,回家却变成了一种互文:“我要回罗马,结束我的剧本,一个人总得结束该结束的东西。”离开,回家,在那一刻,波尔就像尤利西斯一样,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大海在前面,这是荷马史笔下的大海,这是电影《奥德赛》里的大海,这是史诗中的大海,这也是现实中的大海,大海深处真的有一个家?真的有等待自己的妻子?真的有剑光里的杀戮?波尔曾经也面对这一片大海,那时他说:“我们的喜悦马上变成泪水,直到我们靠近大海。”仿佛是一句预言,为什么会有泪水,为什么会在靠近大海时会有泪水?似乎是将《奥德赛》的故事移植到了现实里,尤利西斯在回家之后杀死了那些向妻子珀涅罗珀求婚的求婚者,当夫妻团圆他不应该有悲伤的泪水,但是在这个故事里,争议的地方是:尤利西斯参加特洛伊战争是不是因为无法忍受妻子?或者说,尤利西斯已经觉得妻子不忠了,这是美国制片人普罗可修的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讨论中,弗里茨·朗却认为,不是妻子背叛了尤利西斯,而是她“蔑视”尤利西斯。背叛和蔑视,变成了两种阐述,也正是这相异的解读,使这个剧本走向了两种可能的结局,而对于现实来说,波尔和妻子卡米尔的爱情也在蔑视和背叛中走向那一片流泪的大海。
互文的故事,在摄像机里,也在摄像机外。女人拿着手慢慢地行走,旁边是在轨道上滑行的摄像机,画外音出现,“安德烈巴赞说:电影取代了一个跟我们的愿望更融洽的世界,《蔑视》讲述的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画外音制造的是间离效果,之后摄像机接近镜头,并转向镜头,这一转向很明显的暗示是:镜头对准的是现实,观众可能是演员。这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加上旁白引用巴赞的话来解读《蔑视》,这个多重文本互文的故事就显示出它的层次:电影《奥德赛》构成的是第一层文本,剧组正在这里拍摄根据荷马史诗改变的电影《奥德赛》,围绕着这个电影,美国制片人普罗可修、导演弗里茨·朗、编剧波尔进行过讨论,并力图改编剧本。
在这第一个文本里,就有过大家不用的观点,最主要的是尤利西斯的妻子是否还爱着他,而这也决定了尤利西斯回家的心态,以及杀死求婚者的真正用意。无论是妻子的蔑视还是背叛,最后尤利西斯都拿起了剑,当着最后的结局出现在电影里的时候,引申出了在第二层文本里的讨论,“杀人不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对第一层文本的拒绝,这个结论在第二层文本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波尔和妻子卡米尔回到公寓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坐在浴缸里的卡米尔读到了一本书,书上说:“我们必须反抗,但是杀人不是解决的办法。”第二次提到是在卡米尔和普罗可修乘坐快艇离开拍摄地,波尔和弗里茨·朗讨论尤利西斯的时候,提到他最后拿起剑杀死求婚者不能解决任何办法。
这两次的强调,其实是为第二层文本的结局做一种互文式的铺垫,不管尤利西斯的妻子是蔑视还是不忠,总之,尤利西斯最后杀死了求婚者,而在波尔的故事里,他曾经可能会和尤利西斯一样展开杀戮,因为他出门时带了一把枪,即使那把枪在船上掉了,女助手捡到之后有还给他了,而在他和妻子卡米尔争吵时,从平台走向海湾,直到卡米尔裸体游泳时吗,他身上其实一直带着这把枪,甚至在争吵可能升级的情况下,失去理智的波尔会拿出那把枪,朝向卡米尔,如果再进一步,他还会指向和卡米尔暧昧的普罗可修,那么,波尔就变成了现实中的尤利西斯。
但是,他没有杀人,在主观上或许缺少这一种丧失理智的冲动,和卡米尔发生争执对于波尔来说,更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被蔑视的感觉。而在客观意义上说,他也没有了拿枪杀人的机会,因为在卡米尔游泳之后他靠在岩石上睡着了,仿佛做了一个梦,等他醒来是卡米尔留下的纸条:她把枪里的子弹拿掉了,她和普罗可修离开这里去了罗马,最后是“保重”,是“永别”。他没有能够杀人,他也不会杀人,因为杀人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最后他没有成为尤利西斯——即使他最后和弗里茨·朗告别去罗马,他也没有最终以回家的名义和卡米尔重归于好。
也许在波尔告别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卡米尔其实已经死了,死于一场车祸,当普罗可修和卡米尔开着豪车离开,在加油站加满了油之后,却被一辆槽罐车撞上,双双离世——豪车卡在了卡车的中间,两个人朝着各自的方向死去。一场事故,一次意外,和杀戮无关,和复仇无关,甚至和蔑视无关。所以波尔和卡米尔故事所构筑的第二层文本几乎是在逃离第一层文本,也是在这个逃离意义上,使得“蔑视”这一种情感变得复杂,它无法用杀戮的方式解决,也就是两次强调的那个结论:杀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复杂的蔑视,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回到波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在前一个晚上,赤身裸体的卡米尔还在问波尔,你是不是爱我整个人?从脚到屁股,从乳房到乳头,从大腿到膝盖,卡米尔躺在床上,一个个地问过去:“你喜欢吗?”而波尔也是一次次地重复:“我喜欢。”这是一个真爱的夜晚,不掺杂任何的外来因素,只有两个人。但是,似乎也有了暗示,当卡米尔赤身裸体的时候,旁边的波尔却穿着衣服,盖着被子,一种肉体被遮蔽的状态,其实和卡米尔开放身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两个人在情爱意义上,是不同步的。
这只是一种暗示,当第二天上午卡米尔去见母亲并陪母亲吃了中饭,而波尔去片场和普罗可修讨论改编剧本的事宜,之后卡米尔也去了那里,也就是从他们重逢在片场之后,两个人的隔阂便出现了。一开始是普罗可修邀请大家去吃饭,车子似乎不能做太多的人,波尔提议卡米尔坐上车,然后自己坐出租车,而女助手则骑自行车。三种交通方式,又是一种相异的隐喻,提前到来的卡米尔在等待了半个小时后才看见波尔抵达,她问为什么这么迟,波尔说没有及时看到出租车,之后又遇到了车祸,但是卡米尔显然已经开始不高兴了,而且显示在了脸上。镜头闪现了刚上车时的情景,这是卡米尔内心活动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她开始滋生了所谓“蔑视”的情绪。
波尔说要去上厕所,卡米尔却看到他和女助手在说话,并有某种暧昧的动作;回到公寓后,卡米尔便告诉他不想去卡普里岛的片场,波尔想不明白原因;之后卡米尔的母亲打电话来,波尔接电话却说卡米尔出去了,听到对话的卡米尔为波尔的撒谎而生气,而波尔只是想测试中午是不是真的和母亲在一起……卡米尔的情绪变化是明显的,所以波尔几次问她怎么回事,是不是刚才发生了什么,卡米尔一直回避正面回答,在两个人的公寓里,事件渐渐升级,一开始是观点不同,后来是争执,最后卡米尔对他说:“我蔑视你,这就是我的感觉。”这是第一次提到“蔑视”,对于波尔来说,问题是,昨晚还好好的,早上出门还好好的,为什么去了片场之后,为什么遇见了普罗可修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卡米尔说到“蔑视”,似乎是一种不屑,一种鄙夷,是自上而下的俯视,那么,从“你爱我整个人”到“蔑视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波尔找到普罗可修这位美国制片人,在同意改编剧本的情况下普罗可修向他开除了一张支票,那么蔑视的一种解读是关于钱。在波尔和卡米尔争吵的时候,也说到了钱,卡米尔说,以前写侦探小说,钱不多,但生活并不坏。但是在和电影制片人认识之后,似乎情况发生了改变,波尔一直解释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为了买下公寓,是为了卡米尔,所以这是一种分歧;在这一天,卡米尔似乎看到了波尔的暧昧举动,听到了他的谎言,是不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以前发生过,这是对于情感的一种背叛,也就是说,那晚被遮掩的身体有了一个解读的理由,而这也是卡米尔产生蔑视的原因;第三重分歧大约是对于爱的理解,卡米尔需要的是彻底的,纯粹的爱,但是无论是公寓还是创作,波尔的爱其实已经建立在物质意义上,甚至卡米尔也成为物质之一,在内心一段心理活动中,波尔说:“如果她死了,我也就失去了我的爱。”而这正是他对“杀人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解,而卡米尔的内心想法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死在他怀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卡米尔看来,这种蔑视一开始只是一种情绪的表露,甚至自己也不甚清楚蔑视是不是意味着不爱,即使当两个人开始有了争吵,卡米尔说了一句:“我不爱你了,没什么可解释的,一切结束了”也并非是真正彻底地变成了仇恨,之后一起在卡普里岛,种种不愉快,种种隔阂之后,卡米尔在那个被太阳照见的平台上,面对着波尔依然裸着身体,像那一晚面对波尔时一样;在海湾处,卡米尔也是脱光了衣服,在波尔在场的情况下裸身入海。
蔑视,只是蔑视,但是蔑视的可怕是冷漠,是隔阂,是分歧,最后甚至真的是仇恨。那一句的“保重”和“永别”,是卡米尔写给波尔的留言,但是在她走向普罗可修的过程中,也并没有真正像尤利西斯的妻子一样,被认为是不忠,戴着墨镜,语言不通,就是她和普罗可修之间无法真正在一起的隐喻,而最后死于车祸,则是一种分离的状态。但是,无论是卡米尔的蔑视还是最后的死亡,似乎都和普罗可修有关,也就是这个被贴上“美国制片人”标签的人,引向了第三层文本。
电影《奥德赛》在拍摄,波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发生在摄像机前,而当镜头前出现摄像机,就代表着《蔑视》之外还有一层文本,那就是这个名为《蔑视》的电影之外的现实,波尔为什么要接手改编剧本的活,大约是钱不够用,而他改编剧本一定是为普罗可修服务的,也就是说,波尔代表的意大利或者欧洲电影,而普罗可修代表的是美国资本,这就是电影时代的一个隐喻:在资本之下,电影该何去何从?代表美国资本的普罗可修其实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所以波尔在和弗里茨对话是说他是“独裁者”,而弗里茨说,就像尤利西斯,是简单、聪明和强壮的男人,所以卡米尔代表的纯粹对波尔的蔑视,其实是艺术电影对好莱坞商业模式的蔑视,而最后波尔终于决定回到罗马结束剧本的改编,像是一次在创作意义上的“回家”,但是卡米尔却被一种客观发生的车祸夺去生命的时候,蔑视是不是也代表着一种无法找到出路的迷惘?
那晚他们躺在床上“爱我的整个人”的时候,光线的滤镜分别是红色和蓝色,以及最后的自然光,似乎就是对法国和美国国旗颜色的一种隐喻,电影在这样的镜像中,到底是走向好莱坞式的商业电影,还是继续坚持回家式的艺术电影?其实答案或者是显露在第三层文本里,为什么戈达尔要把摄像机对准观众?为什么要产生间离效果,因为他要制造的是摄像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好莱坞的梦境构筑是隐藏摄像机,而让摄像机对准摄像机,把摄像机带向剧情,甚至把《蔑视》直接放在电影里成为其中一个文本,就是为了像卡米尔一样显露出每一个值得爱的地方,袒露无疑,才是真实,才是纯粹,而这也是对于好莱坞,对于金钱,对于“谎言市场”的一次真正“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