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Siddartha(DhritimanChatterjee)被迫中断了他的医学研究,因为他的父亲没有预料到他的死亡。相反,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在一次工作面试中,他问了一个在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世界。他的回答是(文/鬼脚七) 说《敌手》是一部被忽视的重要作品毫不为过,在经历了对于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的关照之后,雷伊开始关注更为深入的东西——人,人的心理状态,人和周围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境况,而在技巧上,超现实主义和先锋手法的运用也出现在这部影片中,这些“安东尼奥尼式”的主题和“雷伊式”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就是《敌手》所呈现的独特气质。 对于影片主人公悉达多而言,雷伊赋予他的身份是多重的,因为父亲的去世而辍学,找不到工作,爱情的缺失,亲情的疏离,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于城市和生活的恐慌,这种焦虑的状态是很致命的,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人来说尤其如此。在影片开场不久的面试当中,悉达多面对主考官的提问“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回答是越战,进而解释越战比登月更重要是因为越战“展现了人民的力量”,主考官继续追问“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悉达多则不置可否。在这里,悉达多的个性显露无遗,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考和想法,却无处施展,对于政治有强烈的关注却又拒绝参与(在接下来的一场戏中他拒绝了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朋友的邀请),这种带有强烈激情却又犬儒生活着的青年人形象无疑是来自新浪潮的。我们只消看看悉达多穿行在加尔各答街头的样子就知道了,戴着墨镜,不急不慢,沿着街头踱步,时不时地东张西望,这个镜头放在巴黎不就正是利奥德或者贝尔蒙多的最好化身吗。雷伊在这里赋予了悉达多一种外来者的气质,他和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使得他越来越边缘化,他无法在社会里找到容身之所,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天“只能在太阳下不停地走”。雷伊用这种方式展示这悉达多这种状态的的普遍性,或者说,悉达多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整个“人民”的状态,这种混乱、焦灼、带有新现实主义影子的贫乏、以及被社会压榨得不堪重负的人,正是印度社会的普通群众。 影片名为“敌手”其实充满了一种悲壮的意味,和整个社会对抗的正是悉达多自己,孤身一人的自己。雷伊一点一点剥离了他周围的人,最后让这个青年的怒火喷涌而出。在影片一开始的镜头中,悉达多身处父亲去世后的葬礼上,熊熊燃烧的火焰极具象征意味地暗示出在他内心深处燃烧的不满,但是这种暴虐的气息直到影片最后爆发之前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与其说是悉达多一直在努力克制,不如说是他的教育背景和现实情况使他完全没有机会发泄这种不满。悉达多的妹妹因为在工作中和老板关系走得太近,让家里人非常担心,觉得这“丢脸”,悉达多于是自己去找妹妹的老板谈话。在老板走进房间的时候,影片插入了悉达多的幻想镜头——突然站起来对着老板连开几枪,以报复他对于妹妹的“侮辱”,然而现实却是,老板的一句“你还没工作吧”击中了他的软肋,画面上的悉达多被挤在角落里,被富有的私营公司企业家完全压制。这是一种传统道德的压制,悉达多没有工作,无法供给家庭,这就导致了他的权力丧失,导致了他没有资格讨价还价。这是他的最大苦闷,没有工作代表了一种对于家庭和生活的不负责,这对于同处东方文化的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同时对于悉达多自身来讲意味着生活的寒酸,他甚至没有钱去修好自己摔坏的手表。但是同时,他又不能容忍自己作奸犯科,面对从红十字会捐款箱中偷钱的朋友他义正言辞,而另一个朋友带他到一个女人家里寻求“欢乐”时他却择路而逃。悉达多正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必然是痛苦的,既没有力量和社会抗衡,也拒绝和周围同流合污。 影片的后半部分,面对妹妹向富人的“妥协”,堂哥参与了革命,朋友们都浑浑噩噩,悉达多心灰意冷。这种状态正是我们在欧洲电影中常见的人物处境,人物或者选择纵情声色以麻痹自己,或者选择奋力一搏自我毁灭。对于悉达多来说,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爱情。其实准确说来这并不算是爱情,只是渐生情愫而已。在悉达多和女孩在餐厅吃饭的一场戏里,两人讨论“人和人都是一样的”这个话题,借着生理学讨论的幌子,雷伊实质表明的确是人和人地位以及尊严的平等问题,这一绝妙的暗示也为悉达多最后的疯狂行为做下了铺垫。对于悉达多而言,面对女孩的好奇提问,他一次次地解释,人和人都是一样(平等)的,这是他的真实信念,但是当他面对现实的时候,他却发现他无法和别人一样,阶级贫富职业都成为区分人与人的界限。所以最后当他面对又一场面试主考官对应聘者的恶劣待遇时,他爆发了。事实上,我们回过头来看,等待面试的人没有椅子坐,这件事并不值得大发雷霆,但是对悉达多来说不止如此,在这里,再次插入了他的幻想,一个个的应聘者都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在悉达多看来,基本权利的丧失使他失去了为人的资格和尊严,这让他最终爆发,冲进办公室大闹一场。 正如前面说到,雷伊的这部作品是非常“安东尼奥尼式”的,但是也没有放弃印度本身的现实问题,家庭、社会贫富、传统道德等等问题仍然有所涉及。在影片最后,悉达多选择了屈服,离开加尔各答,去到南方做一份推销员的工作。然而就是在远离现代城市的地方,他又重新找到了他一直苦苦追寻的童年时候听到的鸟叫声。这个代表着纯真和幸福的意向和他与女孩保持着的通信一样,形成了影片在结尾部分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丝温暖。原载《看电影》2013年10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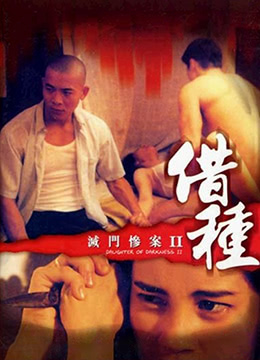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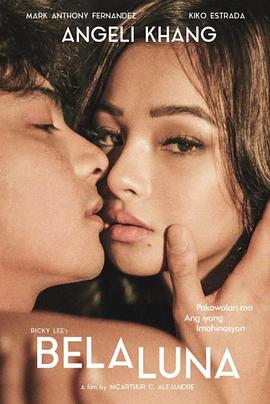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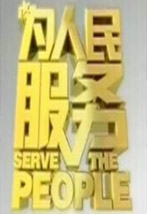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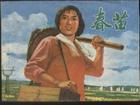


正义者影评